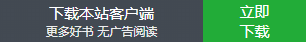第二百二十章,挟天子,令诸侯
第二百二十章,挟天子,令诸侯
谢鲲知道,若王烈真是那人之后,那么这件事情如果被他的仇家知道了,必将要引起一场动乱,甚至祸及整个北地。
谢鲲知道王烈隐忍,在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基本上会选择克制;但谢鲲却更了解他的那位仇家,他是不会放任王烈继续在北地壮大、将来再对他反戈一击的。
他既然连兄弟都敢杀,就绝对不会在乎杀一个后辈子侄,更何况这个后辈子侄对他未来的威胁是如此之大。
而且,最主要的是王烈的先辈的风评并不好、不单单结下了这么一个仇家,若众人知道王烈是那人的后代,肯定会引得各路仇家前来,王烈也将平白树立起很多强大的敌人。
这样,将对王烈未来的发展造成很大阻碍,所以谢鲲必须装做什么都不知道,而在谢鲲想明白这一切之前,身上就已经打上了王烈的烙印,他若弃王烈于不顾,那么自己也将名声扫地。
而且,就算他能跟王烈甩开干系,以江左那些人的xìng格,在大晋也很难再有他的容身之地,除非他肯去投靠刘琨、或者效忠司马邺。
不过刘琨是王烈的老师,他若弃其弟子不顾,当老师的会如何对待他也可想而知。
至于司马邺,在谢鲲看来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更何况还有麴允、索琳这样的权臣在侧,用他来扯虎皮、增长一些人气还是可以,但指望他给谢氏带来机会,基本没有这个了能。
而且谢氏的根本现在都在江左,自己就算能顺利投靠司马邺,那时候手下无兵无权,留在江左的谢氏族人必遭迫害,自己岂不就成了谢氏的千古罪人?
所以,无论从大义还是sī立的角度,谢鲲现在只有一个选择,不管王烈是何出身,都要帮扶他继续向上,那样才符合谢氏的利益。
见谢鲲一直沉思、默默不语,宗敞也不去问,只是笑道:“幼舆,这一步棋你可想得太久了。”
他却知道自己这位老朋友的xìng格,若他说了不知道,你就算把刀架在他脖子上也问不出只言片语。
虽然,宗敞也很好奇王烈到底是何出身。
谢鲲闻听宗敞调侃,却道:“我与坦直你不同,我现在顾虑颇多,每一步都要走好,否则全盘皆输,还要连累无辜啊。”
宗敞闻言,哈哈一笑,也不说破。
有些事情两人心知肚明,就无须再谈,而是专心手谈,王烈那边也自去会见贵客,不用他们操心。
只是,现在看,却已经有人对王烈的身世起了疑心,而在这长安城暗中涌动的bō澜,却正是他们所兴起的第一bō诘难而已。
只是,如果一旦猜测变成了事实,那等待王烈的就绝对不会是这般容易躲避的流言蜚语了。
而王烈似乎对这些还一无所知,至少他并不急于强求了解自己身后的故事。
相反,在关中月下阁内,那百炼铁器坊的老者一见程翯,就说与她家时旧交时,王烈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到是程翯,微微错愕,有些担忧的看着王烈。
~~~~~~~~~
程翯正要说话,那老者却道:“程家小娘,你不用担心,老夫并无恶意。其实老夫当年你家祖和我同朝为官,可后来他无心为官,退隐江湖,却留下我这个醉心名利的家伙独自厮hún。呵呵,往事如云,不提也罢,咱们单独论交,不牵扯你的祖父,你称我伯父即可。”
老者说这番话时,却一直用眼睛瞄着王烈,希望从他脸上看出什么端倪,王烈却如老僧入定一般,做在那里,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
程翯此刻却无这样的好耐心,她到不是担心这老者故意说谎期满,因为自己现在身份与老者相差甚远,他还不至于编造这样一个无聊的理由,让自己当他是长者,这样对老者并无什么好处。
程翯担心的是王烈,因为她祖父的事情她多少有些了解,而她却一直没有对王烈说,生怕王烈以为自己是有意欺瞒,为此生气。
此刻,王烈面无表情,但心里却在急转,程翯的家祖自然是那青山村的村正程平,王烈也一直不相信那样一个气度、xiōng怀若谷,见识不凡,能和当年的常山郡太守直接对话,维护青山村利益的长者是土生土长的农夫,甚至可能连程平这个名字都是化名,包括自己的父亲王抗,就一定是叫这个名字么?
但程平不说,王烈就绝对不会去问,包括他和自己父亲王抗之间的关系,这些东西王烈很清楚他们脱离不了干系,但却丝毫没有埋怨他们的意思。
在王烈看来,这些事情的内幕就算自己当年就知晓,也不会对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实质的改变,反而会让自己学会怨天尤人,不思进取。因为当年既然王抗选择了隐居青山村,那就只能说明自己的身份不可见人,如果暴lù甚至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前世熟读各类家斗、宫斗等狗血小说的王烈自然清楚,在自身没有足够的能力前,保持低调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事情。而且凭借自己的努力步步向上,却比仰仗家世上爬要更符合王烈的价值观。
既然不能唾手可得一份家业,那就索xìng摧毁这旧有势力,创造一份自己的基业。
不过眼前的老者虽然明了其中一些内幕,但似乎也并不想多言,和程翯说了几句,就不再提程翯祖父程平的事情。
而且,既然他了解程平,却也应该知晓王烈的一些事情,也是绝口不提,似乎对王烈没有什么兴趣一般。
老者说完,笑眯眯的看着王烈,眼神中充满鼓励,似乎在说:“你问我吧,问我我就都告诉你……”
然而,让他失望的是,王烈似乎好无所觉,依旧是那副镇定自若的模样。
过了半响,抬眼看了一脸担心的程翯一眼,轻轻mō了mō她的秀发,然后起身道:“长者,既然大家都是旧相识,我们之间就开诚布公、长话短说。其实烈今天来只有一个问题:就是长者与我无亲无故,就算看在阿璎家祖的面子上对我友善,但又怎么赔本为我军打造盔甲,这千金之赠实在巨大,小子心下忐忑,生怕不能还长者恩情?”
老者闻言,心中暗道王烈狡猾,但既然对方不想求自己,那自己也不能巴巴的去主动说什么。
沉吟片刻,却是笑了起来:“呵呵,王将军真是客气,难道我身为长者就不能赠送小辈一点礼物么?”
王烈摇摇头,认真道:“礼物可收,但人情不可拖欠。做人应量力而行,我自觉对长者无甚功劳,长者却如此不计回报的厚待我,如果将来长者一旦提出一个需要我帮忙的条件,这条件我还很难满足您,您说小子我是做还是不做,到那时小子若不做,岂不是要担上忘恩负义的名声?”
那老者一听,无奈苦笑:“我那乖女不是被你欺负的写下约定了么?”
王烈道:“约定只是俗成,而且那只是个笑谈,毕竟长者才是真正做主之人。”
老者听到这里,气的一摆手:“你个小滑头,真是一点把柄不想留给别人好吧,我这里答应你,将来绝对不提让你为难的要求,你也可以随意选择答应不答应。怎么样,还有其他疑问么?”
古人最重誓言,尤其是老者这样自命清明的人,王烈其实已经猜出他是哪一个,却是故意不说,见他答应了,却道:“长者在上,多谢长者厚待,请受王烈一拜,烈就此告辞。”
老者却有些愕然:“怎么,你这就走了,你就这么相信我,而且不想知道我是谁么?”
本来,这老者打的是今日一来,就先和程翯拉近关系,引王烈相询,自己也好判断一下王烈到底是何出身,然后闻言细语加以安抚,最后再亮出自己的身份,让王烈主动提出条件,还报自己的恩情。
但哪想到,这个王烈根本不按常理出牌,不但全无好奇之心,而且也不管什么长者在上,恭敬顺从,却是逼得自己也说出今后不再麻烦他的话。
而得到了这些的王烈,不但不欣喜敢接,却是拜了一拜,就想开溜。
“这是个什么少年……”老者心下气得内脏俱疼,但表面上却还要微笑如一。
此刻,听得老者疑huò,却嘿嘿笑道:“长者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长者如果想寻找一个盟友,那我可以考虑。”
那老者闻言一震,这才醒悟过来,原来面前这个小滑头早就猜出了他的心思。
他还没说什么,一旁一直看着这一切的阿秀忍不住插话道:“你这家伙真是自大,我父亲好心送你盔甲,你应当感jī才对,如今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表面上说不想亏欠我们,其实是想让我们主动把这恩情取消,如此行为,难道不算是虚伪么?而且,你竟然还想做我父亲的盟友,你知道我父亲是什么人么?”
王烈看着少女的娇颜,这女孩子其实是个蛮可爱的姑娘,虽然聪明,但却一副涉世未深的模样,说话虽然有时候冲了一些,但一看就是个温柔的女子,她这一问,气氛反而缓和了不少。
王烈却温声道:“小娘子,这件事情上我并没有强求,如果长者觉得我无礼,可以不答应,我也不想占长者恩赐的便宜;但是现在一切皆是长者自愿,你情我愿的事情,你怎么好单单指责我呢?而且你所我虚伪,长者恩赐我这么说,却说什么都不需要我做,可我却知道他需要和我结盟,获得我的帮助,你说这算不算虚伪呢?”
少女闻言,有些语塞,明知道王烈这话里是狡辩之词,但一时却有抓不住他的毛病。
老者无奈的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儿,自己这个义女却与自己那个死去的亲生女儿有些不同,自己那长女是外柔内刚,与人温和,但却极有主见。
而这个义女虽然xìng格温柔,但却是心高气傲,因为年少时就遭遇颇多磨难,所以养成了敏感、易冲动的xìng格,可正因为她没有经历过这权贵之家的黑暗与内斗,所以内心里还是一片天真烂漫,一旦与人争辩,既不会刻薄言语、也不会自我辩白,却是落了下风。
之前,他曾告诉她不要和王烈争执,但她却好像一直想要在王烈那里争辩出什么一样,却依然被王烈顶的说不出话来。
但自家的孩子自家爱惜,尤其是少女身世可怜,是老友唯一的血脉,自己这一辈又再无女儿,老者一直拿她当宝贝一般,却是笑眯眯道:“王将军,小女不懂事,你何必与他争辩,你说的不错,我给你盔甲的优惠,却正是有事相求。”
王烈立刻一咧嘴,灿烂笑道:“长者请讲”
老者道:“王将军,你对我实话实说,你现在究竟想和哪一方联合。”
王烈奇怪道:“长者是什么意思,是指我和其他铁器坊买卖么,盔甲我已经在您这里买好了,到是有些地方需要修改,我也不准备找其他铁器坊了,就由你们负责回炉改造吧……”
老者无奈道:“王将军就不用装糊涂了,我问的是你究竟要站在司马保一边,还是麴允和索琳一边,又或者是其他势力一边。”
然后,满脸期待,等待王烈回答。
王烈却一咧嘴,笑道:“长者身居江湖,却心忧庙堂之事,看来我大晋处处都有布衣侠士,佩服佩服。”
老者气得一拍脑袋:“王将军,为何如此调笑老朽。”
王烈却正sè道:“长者一直不肯告诉我您是谁,我只当你是个商贾之家,又怎好怨我?”
却是完全把老者刚刚和程翯对话中提及的同朝为臣忽略掉。
老者气得一拍桌子:“你个孽障,真是气死我了。”
一旁的少女一边劝慰老者,一边不满道:“王将军,你和我斗气也就罢了,为何还要气我爹爹,你看你把他气的?”
见老者一副吹胡子瞪眼的模样,但眼中却并无怒意,还在偷眼看王烈的表情。
王烈一看,心下暗笑,这老者一直不说自己身份,一涉及到关键就避而不谈,却希望自己竹筒倒豆子,哪里有这样的好使。
但对方毕竟是长者,而且对自己还有恩惠,怎么都要给对方留一点情面,却是该见好就收,于是王烈忽然拜倒:“长者果然气度非凡,不愧为我大晋栋梁之臣。小子无礼,刚刚只为看到长者真心,既然长者是一片赤诚,那小子也不敢再继续隐瞒,也如实相告于长者。
烈此次来长安不为名利,只为这幽州未来的发展,和我大晋的安危,至于和哪一方结盟,恕我直言,这些人我还都未看上眼。”
老者闻言,笑道:“我大晋堂堂的亲王、右丞相,还有那自命不凡的卫将军,尚书仆射,却无一被你一个五品官员瞧上眼,若被他们知道还不要吐血?”
然后,又认真对王烈道:“这些人你都看不上眼,但不知道将军想与什么样的人结盟。”
王烈看了老者一眼:“烈心中只为大晋,南阳王与两位尚书仆射大人虽位高权重,却皆非良木,我却只想为至尊尽心竭力,以至尊为盟友,以匡扶社稷江山为己任。”
老者闻言,却是一愣,片刻道:“小友大志,可是现在你连至尊一面都不能见,何谈这许多?”
一旁的少女却忽然道:“说的一本正经,其实就是狭天子以令诸侯,学那前朝的孟德公所为,当然本朝也有此例,王将军此举并不新鲜。”
老者忙清咳起来,程翯也是一惊,看向王烈。
王烈却是面sè微变,本来准备好的话全部咽了回去。
却再次细细打量这少女,只见少女青丝如云,眉眼如画,灯光下不断眨着大眼睛,盯着王烈,丝毫不觉得自己说了什么惊世骇俗的话,依旧是那个天真烂漫的可爱佳人。
王烈暗叹一声,这少女的确聪慧,不失天真可爱,刚刚应该也只是顺口说出,可若被有心人听了,定要寻她麻烦。
片刻,老者对少女道:“阿秀,休要胡说,王将军乃我朝忠义,岂会行jiān臣之事?”
少女不满道:“这不是jiān臣,此乃枭雄之道,难得爹爹认为我朝太祖之父是jiān臣么?”
老者闻言,气的怒道:“不要说了,这等事情我相信王将军是断断做不出的。”
眼睛去始终盯着王烈的手指,看他那修长的手指不断在面前抖动。
王烈的手慢慢抚过面前,忽然mō向腰畔,老者的心都到了嗓子眼。
王烈却是忽然伸展双手,抻了个懒腰,笑道:“阿秀姑娘真是太看得起我了,我不过是一个寒门小卒,侥幸到了现在这个位置,能保一方平安就已经是功德圆满,岂敢再有奢望?”
老者犹豫着要不要喊人进来的时候,少女不满的看了故意唬人的王烈一样,忽然又道:“爹爹,你又何必怕他,就算王大哥是您口中的jiān臣,但jiān臣与jiān臣也有不同,有的那jiān臣一心为己,自sī自利、心狠手辣,却是不可交;但有些jiān臣却是眼见朝政糜烂,权贵昏聩,这才心怀天下,只是野心大了些,对朋友和兄弟都极好,这样的人未必不是万民之福,而王将军不正是这样的人么?”
老者闻言,不满道:“阿秀,你怎么可以妄谈朝政?你也是大丫头了,怎么能如此幼稚,你了解什么……”
阿秀却道:“我不了解许多,但我知道我那可怜的爹爹是如何苦盼朝廷援军不到被叛军杀死的……王将军,我听闻当**大战石勒,你的兄弟万里迢迢都去救援你,和你们这些英雄相比,这个朝廷的某些人岂不更是jiān佞之臣?”
老者大怒:“够了,不要再说了——”
见父女两人争执起来,王烈却忽然表情一松,笑了起来。
那老者看了王烈一眼,假装气道:“你们真是气死我了,我出去透透气……”
王烈去起身道:“梁司徒,这个时候您是想出去叫人来抓我,还是想要趁机遁走,不再与我叙谈?”
王烈这话一出,那老者终于sè变,片刻道:“小子,你早就知道我是谁,却是故意装糊涂。”
王烈笑了笑:“这长安城还有哪个高官为梁氏?更何况司徒大人也是名满天下,小子虽未见过,但见大人超人风采,却也能猜出几分。”
老者却正是那大晋司徒梁芬,但他此刻听了王烈赞美,却毫无高兴之sè,反而道:“现在知道了我的身份,王将军想要杀人灭口么?”
王烈双手一摊,诧异道:“司徒大人何出此言?您是我朝重臣,我又以匡扶社稷为己任,怎么能做屠戮柱石的事情,而且这可是在司徒大人的地盘,小子我活的不耐烦了么,敢对司徒大人不敬?”
梁芬闻言,却是哭笑不得:“早就听说你王烈胆大包天,就没有你不敢做的事情,你现在却和我卖起了乖,真是岂有此理。”
语气虽是埋怨,但气氛却缓和了许多。
王烈却道:“其实,梁大人心中所想,烈也能猜出几分,不知道大人相信不相信?”
梁芬闻言道:“我梁芬也活了六十多岁,过了huā甲之年,自信也做到了喜怒不形于sè,你又如何知道我想什么,年轻人聪明是聪明,但莫侥幸用大话诓骗老者?”
那少女阿秀也道:“就是,爹爹,我看它就是有意诓骗你,咱们走吧,他不敢动手的,今夜多少人看他走进了这个屋子,您若有意外,至尊饶不了他的。”
王烈听阿秀这般说,却哈哈一笑:“是不是诓骗,听我说了才知道,而且阿秀姑娘,下次说谎底气要足一些,就算这月下阁就是司徒大人的产业,我也不相信很多人会知道他来这里见我,而且我若真有歹意,你觉得你们能有机会走出这间屋子么?我的武功你也见过,可是不低哦……”
说完,故意一呲牙。
少女一看他又摆出这副无赖模样,却是一咬牙,恨恨坐下:“就听你这个大坏蛋能说出什么理由来。”
少女此刻对王烈的情绪很矛盾,即觉得他是个英雄,也正是自己心中所想的那般英武潇洒的模样,甚至还希望他将来能为自己报仇;可是又觉得他实在惫懒了一些,而且有些滑头爱欺负人。
王烈却盯着大晋司徒梁芬的眼睛道:“大人无论是结交我,还是给我恩惠,无非就是想要通过我为你的家族别寻他路,而究其根本,却是大人对长安的朝政已经没有了信心……”
见梁芬意动,王烈轻声却坚定道:“梁大人,你不用否认,若想我王烈相帮,就请坦诚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