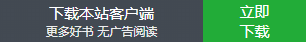第二一七折、映钩如线,片片絮惊
耿照听他口气不善,悬着的心还未落地,差点又蹦出喉间。
堂上只有两人,将军手无缚鸡之力,以耿照现下的修为,便有十个慕容柔也尽都杀了,驿馆里外虽有穿云直精锐驻守,毕竟赶不上两人一座之隔。然而少年却像被蛇盯住的青蛙,浑身僵冷,将军视线堪比灰袍客的“凝功锁脉”,虽非武功,足令一身武功无用。
若是过往,耿照早滴着冷汗、拱手低头,连称“属下知错”,此际却有寸土难失的压力。
无法说服将军,以雪艳青、媚儿袭击将军的旧事,身为七玄盟主的他,即刻便成将军之敌,非但拉不到助力,一个不好便是鱼死网破的局面……一霎间,心中转过无数念头,定了定神,小心翼翼开口:“回将军,此法确非属下所想,是自家姊处学来。”
慕容柔本是讥讽,岂料竟换得了一本正经的回答,又气又好笑,哼道:“仔细说话,莫让本镇再加你个推诿塞责的罪名。我向以看人的眼光自诩,到你这儿,才知什么叫‘行远必自迩’。是你过往藏得太好,还是本镇麾下,真无你发挥处?”
将军难得插科打诨,耿照可没心思接哏,俯首道:“家姊双耳残疾,平日须以手语交谈,我们村里管叫‘道玄津’。属下与姊姊感情甚笃,但儿时总有吵架的时候,闹起了别扭,她打手语我不肯看,我打手语她也扭过头,大伙眼不见为净,谁也不同谁说话。
“其实没多久我便后悔啦,姊姊对我极好,我很欢喜她,只拉不下脸赔不是,净在窗外徘徊。姊姊坐在屋里,背着窗,没过多久,便对着空处打手语,大多是说自己的心情,我在窗外看着看着,心中歉疚,回到屋里同她说话,姊姊便像没事人似的,绝口不提吵架闹别扭的事。”说着不觉露出微笑,彷佛又忆起儿时景况,片刻才敛起笑意,垂首道:“有些事不能说,只能做。此非欺瞒,而是权宜,望将军明鉴。”
慕容柔冷哼一声。“你可知‘真龙’二字,历来是翦除政敌、诛人九族的好借口么?魔宗七玄什么根柢,谅必不用本镇替你恶补一部江湖外史,别的不说,光是‘龙皇祭殿’四字,便足以作几篇血淋淋的文章。将这帮余孽纠集起来,还做了它们的头儿,这是要有几颗脑袋的人,才干得出来?”
“若胤铿做七玄盟主,口出悖逆,属下并不觉奇怪。”耿照早有准备,娓娓说道:“然而鳞族、毛族,俱是我朝之臣,守疆卫土,一视同仁,自独孤氏有天下,未尝有忠忱之士因血裔获罪;北关武登、东海龙庭,无不许以旧有,加官进爵破格重用,可见出身非是关键,能否忠于朝廷,才是荣辱兴衰的依凭。
“况且,鳞族之存,距今已逾千年,现今七玄之中,能明白追索出鳞族血裔之人,十不存一,比将起来,指剑奇宫只怕还要纯粹得多,先帝赐以九曜皇衣,封为侯爵,四海之内皆颂宽仁;今上克绍箕裘,风行而草偃,圣德昭昭,纵有闻风起舞之人,亦难伤圣明,反显用心歹毒,自贾祸端。”
这番话说得入情入理,全以庙堂政争的角度分析,指出“闻风起舞之人”,从来就不是混迹草莽的江湖大老粗。
以此说事,那是把武登遗民、指剑奇宫都拖下水,算上韩雪色的出身,指不定连西山韩阀一并卯上,慕容纵以七玄之主为武胆,这就想栽他个阴谋反逆,怕是牵扯太过。这么蠢的言官,白马王朝开国迄今还没出现过,日后横空出世的机会应该也不大。
慕容柔本是试探而已,听他说得鞭辟入里,又抬出孝明皇帝,词锋虽嫌迂阔了些,将军平素不喜,毕竟拍到了点子上,正要点头,陡地心念电转,轻哼一声,冷笑:“看来七玄之内,的确是有些人才。瞧这会儿,盟主连文胆都备便了,接下来是要开幕府了罢。”
这段话的确不是耿照自己想的,当中就算有他的意思,也决计不是这般口气。
“慕容一直都不是他的人,是看在他那便宜弟弟的份上,姑且用之。每次提到这人,独孤弋总嫌没趣,便冷在边上不说一句,场面都寒碜。”离开冷炉谷的前一晚,耿照唤来了蚳狩云,屏退左右,将心中的盘算一五一十地告诉她时,华服老妇如是说。
耿照并未特别信任这位天罗香的大长老。
若非青面神受创严重,早被白额煞悄悄带离越浦,往金土之气浓烈的秘境修复功体,以致缺席七玄大会,他更相信大师父与二师父;便说为人磊落,薛老神君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怕也在蚳狩云之上。
然而姥姥的城府与手腕,恰恰是他此刻所需,而蚳狩云还有一样旁人不及的好处:出于对独孤弋的关心,比起绝大多数的江湖人,她从更早以前就开始留心东军的崛起,对慕容柔的认识,也绝不仅仅是“镇东将军”。
“慕容柔讨厌江湖人,多半也是因为他。”
对着银釭红焰,轻剔灯花,蚳狩云放落细长的银箸,怡然笑道:“要不是天上掉下个独孤弋,独孤容打出生就是镇东将军世子,独孤阀得了天下,他理所当然地该坐龙床──举凡独孤容身边的人,没有一个不这么想。他后来虽还是做了皇帝,对那些个从龙之臣来说,都嫌迟了。”
“可天下……”耿照只觉无比荒谬:“怎么说也是太祖爷打的罢?孝明皇帝接下了兄长的宝座,虽说也不是没有功劳,非是坐享其成的二世祖,可太祖爷传弟不传子,亦是难得的宽大,还能有甚不满?”
蚳狩云摇头道:“人心不足,也就这样了。人说慕容目无余子,眼底容不下一粒砂,依老身看,此人未必真是如此,只不过他的私欲较常人低得多,才显鹤立鸡群。与这样的人打交道,当他是圣人看待,出手必定落空,把他当成一个要求高得多的普通人,庶几可也。”
“请长老指点一二。”
“盟主客气。”蚳狩云沉吟片刻,正色道:“常人所欲,不过趋利除弊而已,慕容柔也不例外。盟主须教他知晓,与七玄之主合作有什么好处,纵有隐忧,也能轻易回避;利大于弊,以慕容之智,断无拒绝的道理。”遂教了说词,耿照连连点头,大为叹服。
蚳狩云也不与他客气,含笑接受,犹豫了一会儿,又道:“盟主须知,只消是人,便有忌贤妒才之心,越是聪明才智之士,越难跨过这槛。以往慕容对盟主三分倚仗、三分恩宠,看似倍于他人,但始终还扣着四分在手里,猎犬再怎么能干,颈索终究握于猎人之手,是以猎人不惧,放心信任勇猛的鹰犬。
“而今盟主武功盖世,又有同盟势力支持,慕容若觉你与他同逐一麋,那就不能再是猎犬,而是竞争对手,须得小心防范,必要时抢先下手,以绝后患。要问老身的意思,我宁可盟主瞒着慕容,尽力延后图穷匕现的时机,方为上上策。”
但耿照非是出于道德的考虑,才决定对将军坦承一切的。
不明白慕容是如何窥破谎言,根本无从防范。若教将军起了疑心,那才是最糟的事态。
耿照本不以为三言两语之间,便能轻易说服将军,听他淡淡哼笑,一颗心沉到谷底,想起姥姥提醒,忙拱手道:“属下所部,亦是将军的部属,犬马驰驱,敢不效劳。”心念微动,暗自着恼:“糟糕!我回得忒快了些,只怕将军不喜。”
果然慕容柔冷冷一笑。“我可没有这种来历不明的部属!要是认了这桩,从今而后,东海地界近半的江湖仇杀,岂不打着本镇的旗号而行,正道七大派死于魔宗七玄手底的,都该上靖波府讨公道?”
耿照强自镇定,心知老调重弹,至为不妙。本来最理想的状态,是将军顺着先前虚问虚答的调子,轻轻揭过此事,算是允了双方的默契,就像他对岳宸风私下的行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不过问。
无奈慕容柔对他“隔墙说明”、以避嫌疑的好意似不领情,接连数问,无不咄咄,耿照心思虽清楚,要比临机应变的伶俐口牙,岂入将军法眼?越说越僵,不幸正中蚳狩云先前所虑。
他本想再举岳宸风为例,岳贼与五帝窟、五绝庄仇深似海,然而漱玉节、薛百螣也好,上官母女也罢,并未视镇东将军为寇仇,江湖人恩怨分明,到底与朝堂政争动辄牵连的陋习有别;话到嘴边,转念又想:“细数岳贼之恶,何异于指摘将军?毕竟是他默许纵容。况且岳贼身死,迄今还未给将军一个交代,揭此痛脚,益发缠夹不清。”事实上,慕容柔曾要他上缴一份关于岳宸风恶行的报告,耿照粗通文墨而已,差点被这案头任务逼得吊颈,最后还是绮鸳解的围。只是那摞字迹娟秀的卷宗,最终也没能说明岳宸风去了哪,呈入驿馆后再无动静,宛若泥牛入海,一去不返。
耿照想起姥姥“兴利除弊”一说,脑海中灵光闪现,猛地抓住要领,沉声道:“恰恰相反,从此东海清平无事,虽有江湖,亦无江湖。”
慕容柳眉一轩,似没料到有这般回答,尤其“虽有江湖,亦无江湖”八字,极对他的脾胃,只不知是这少年故作惊人之语,抑或真有腹笥,一下子来了精神,冷笑道:“我定是太久没同你说话了,听着都像另一个人似的。莫教本镇失望啊,接着说。”
“有人之处,便有是非;有是非处,便是江湖。”
耿照斟酌着字句,审慎说道:“纵使收缴刀兵,解散门派,不过是由明化暗,强身健体而传技艺,排难解纷而起角争,本是天性,率性而为,绝难禁止。为避涝灾,将河流通通堵起来,乍听是一了百了,实则有施行的困难,真要做成了灾害更大。与其消灭河川以避涝,不如加以整治,调节旱雨,自然无灾。
“七大派之称正道,未必较邪派七玄行事,更加光明磊落,‘正’于何处?说穿了,不过是顺从朝廷,得以节制;至于是为黎民生计,抑或为高官之利而制,得看上头的意思。
“七大派以衙门为靠山,而邪派中人自以为闲云野鹤,没把朝廷律令放眼里,一生龃齵,两边都肆无忌惮,故江湖纷争,无日无之。若将所谓‘邪派’,也如正道一般纳入管理,遇有争端,无不循朝廷规矩求解,虽有江湖,何处不是王治?也与没有江湖,差不了多少了。”
他才说到一半,慕容柔细长的凤目里已隐含笑意,甚且有一丝嘉许的意思,只不知是赞他反应奇快,还是真听进了这套说辞,十分受用。
耿照不敢妄加揣测,只得打蛇随棍上,硬着头皮续道:“此事问诸正道七大门派,只会得到个‘不’字。盖因黑白两道恩怨纠葛,难解难分,凭空掉下来个排纷止斗的禁令,解了他们降妖伏魔的借口,以前能做的,现下不能做了,哪个愿意?将军纵有心将邪派纳入管辖,使其改邪归正,这些所谓正道人士必定多方阻挠,遑论向邪派传达将军的旨意。”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邪派高手们野惯了,要他们木枷加颈,自缚低头,只怕是难上加难。凡是“招安”之前,必先经历尸山血海、惨烈厮杀,待其力竭势衰,始能为之,便为此故。
“除非……”慕容柔不觉微笑,界面道:“有个邪派服膺的主儿,率领麾下,主动投效,方能解此两难之局?”
“也要有清明如镜的主司,大度接受才行。”耿照小心道:“魔宗七玄高手,自来是邪派中最难节制的一群,如今属下已得其五,众人意气相投,知将军心怀天下,愿效棉薄,只求有此良机,必不相违。将军明鉴……”
“慢!”慕容柔举起白生生的右手,眯眼冷笑:“这‘心怀天下’四字,足可杀人,故本镇于此,丝毫不敢放松。”
“……若杀的却是旁人,将军以为如何?”
慕容柔笑意倏凝,连锋锐的视线都于顷刻间消散一空,俊美的脸孔宛若玉雕面具,生机尽绝,自此才显出真正的冷彻。所有的表情、温度……俱都由这张脸上褪去,空洞得不带一丝真实感,然而不知为何,耿照却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慕容柔,他从未像此刻这样,在不经意间露出防备之势,但少年吐出的字句已然无法停止。
“岳宸风可以坏事做绝,仍不牵连将军,盖因他所领俸禄,一直都挂在东海臬台司衙门的名下。属下乃白日流影城之典卫,真要有人为此负责,也该是一等昭信侯才是,与将军毫无瓜葛。”
在绮鸳的报告中读到这一条时,耿照也是错愕不已。难怪迟凤钧迟大人在不觉云上楼与岳宸风同席时,神情会是这般无奈;将军欺他,可说得上“过份”两字。
若说“虽有江湖,亦无江湖”的理想是诱之以利,耿照的客卿身份,便是除弊的一着妙棋。真要有人追究起来,查证之下赫然发现:耿照根本就不是镇东将军的部属,他的顶头上司乃是流影城主独孤天威,以独孤天威跟平望都小皇帝的深厚交情,要栽他这条谋反的罪名,怕连指控之人自己都不信。
“这虽不是慕容柔那厮重用盟主的主因,但毕竟也是原因之一。”
从耿照处听闻此事,蚳狩云安慰他之余,亦不忘指出关窍:“这就是慕容柔的习惯,有了习惯,就有破绽。他不是贪图小利,想省些粟米银钱,才将客将寄于他人名下,而是这人小心惯了,他不信任江湖人,却舍不了江湖人的好处,为保自身,才从他处借将来用。攫此破绽,便有可乘之机!”
(我……抓住那个机会了么?)
短暂的沉默,对阶下俯首的少年来说,彷佛有一季那么长。
倘若可以,他并不想与将军这般赤裸裸地角力,把这些心机城府全摊开来说,只要信任将军的决断,全心执行命令就好。可惜将军的蓝图并不是他的。猎犬与猎人的关系,不仅会在“同逐一麋”时决裂,各自拥有不同的目标,也将使他们走上歧路,从此分道。
将军察觉这点了么?他能不能──或说愿不愿意──同注定分歧的对象合作?
直到将军轻声笑了起来。
耿照猛然抬头,恰迎着那双含笑的姣好凤目,慕容柔掸了掸扶手,淡道:“惊险过关哪,耿典卫。你说了这么一大套的笨话,还好有一句足够聪明,本镇一向不用蠢人,现在我勉强能相信,你或有节制麾下的能耐,不致被人牵着鼻子走,在对付幕后的阴谋家时,不会一声不响地便丢了性命。”
“多……多谢将军。”耿照愣了片刻才回神,一抹额汗,所费心力丝毫不逊于一场剧斗。
慕容柔敛起微笑,正色道:“你隔墙说话的心意,我能明白,然而本镇从不浪费时间玩这等小把戏,我能看穿他人说谎,但我要说起谎来,谁也不能看穿!以后所有的事,直接向我禀报即可,巨细靡遗,不得隐瞒;七玄盟中的门派组织、高手来历等,我通通都要知道,你的人若是违法犯纪,休想本镇护短。明白了么?”
“属下遵命。”
慕容柔呷了口冷茶润喉,又问:“你方才同罗烨说的,还有什么人知道?”
耿照如实回答:“除同盟中几位长老,还有属下的结义兄长、观海天门教下的胡彦之胡大侠,以及镇北将军的千金染姑娘知悉。”慕容柔点头:“将盟中知情之人,于清册上标出,此后不得再传,违者视同违律,须有个处置。”
“是。”
“在这里,你是我向流影城借调的客将,行事须依军法。”慕容柔道:“公余你干什么去了,本镇无意干涉,就像我从不管底下人做甚消遣,莫违法犯纪便是。然而行军打仗,首重保密,军机不密,十万大军也就是一夜而已,况且敌暗我明,你不能节制手下,便是逼我越俎代庖。须极力避免此一情节发生。”
“……属下明白。”
“你知古木鸢是什么人了?”
耿照悚然一惊。他想过将军或能从自己的叙述中推得此事,只是没想到会是这般单刀直入的问法。在镇东将军出手前,他至少要同“古木鸢”见上一面,亲口问他,关于刀尸……关于自己的一切:为什么是我?我是什么?你们,到底想要我怎样──“看来,你是误会了什么。”
将军淡漠的语声将思绪拉回了现实。
慕容柔起身离座。“……跟上。”掀开青帘,缓步而入。
这不是耿照头一回来到将军办公的内堂。第一次来,慕容向他展示了壁上的巨幅东海地图,吐露他那为君王平定四方、混一宇内的“世间大恶”,耿照为其惊人气魄所折,甘效犬马,从中获益良多。
许久未至,几案上仍是堆满公文,同印象里横疏影的书斋颇有几分相似,但文书的海量不可一概而语。慕容柔命他在四壁燃起牛油巨烛,将堂里照得明亮,书案后的粉壁仍被青布所掩,藏着将军的恶愿与野心──“揭下来。”慕容柔命令他。
耿照将垂于壁前的青色布幔扯落,失声惊道:“这……这是……”
熟悉的巨幅地图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在粉壁之上,贴得密密麻麻的大小纸张,有的是将军几案常备的精纸,也有尺寸不一的纸片字条,全用米粒之类浮贴在墙上;乍看杂乱无章,再看得几眼,才发现纸张似是各自成团,将偌大壁面分割成几个团块,纸张密集处分别写着题旨似的大字,有“三乘论法”、“旧驿遇袭”等十余处标注,当中甚有老胡追查的少女拐带案,显然是在这几个月间,越浦发生过的诸般案件。
纸张上头,不但有朱笔批注,圈起来的字句上还钉着大小各异的钉子,拉起一条又一条的彩色丝纟,将十数个团块上的各种讯息牵引联系,或因果相连,或求同存异,每条线的背后都隐含着巨量的归纳分析,必有深意,可惜过于繁复,无法一望即知。
其中一条较粗的红线吸引了耿照的目光。
这条线通过了将军初到城外破驿的行程,上头列出了知晓这份行程的关系人,继而通过籸盆岭的流民暴乱事件,指向曾捐赠米粮与灾民者;连到征用九转莲台的大跋难陀寺、打款到“三江号”江水盛名下的四极明府委托,以及三江号月来遭窃一案,据说什么也没丢,只有存放陈年旧帐的老库房积灰上,多了几只半截脚印,宛若怪谈,令人背脊发凉……
红线不止通过大部分的团块,也从各团块连到中央“三乘论法”那区,最后汇于一张写满姓字的纸头上。
纸上绝大多数的名号,无论是原有的,或明显是后来才添上的,都被朱笔一一划去;唯一圈起的一个是“迟凤钧”,旁边以朱笔标着“姑射”两个小字,未被杠红的,还有其余九个名字。
耿照在九人当中,几乎找到了他目前已知的所有“姑射”成员,包括横疏影在内。
换言之,即使将军所知远远不及耿照,再给他一点儿时间,又或多些线索,将东海搅得天翻地覆的神秘组织“姑射”,就要被镇东将军慕容柔从幽影中揪出,没有一个人能逃得掉,而古木鸢甚且不觉!
──这……这是何等惊人的洞见啊!
世上真有这样的人……这却又如何可能?
“如你所见,”身后,慕容柔淡然说道:“我不是教你吐露秘密,是确定你知不知道而已。我缺的几处关键,方才在你的叙述当中,俱都一一补齐,这九个名字又能再划掉几笔。”说着踏墩而起,又补缠上几条长长短短的粗红绳,拈起案上半干的毛笔,杠掉几条名字,圈起了“横疏影”、“琉璃佛子”,当然还有古木鸢的真身。
“……是不是简单得很?”
面貌姣好的中年文士下得绣墩,退到案前,仰望填塞了巨量讯息的纸片墙,像解开了极其困难的字谜,又或完成一组繁复的燕几图似,微眯的眼中涌现情感,有得意、有疲惫,也有一丝宽慰般的松弛。“我以前在内……我一直都很擅长这种游戏,看人与排设燕几图,从来难不倒我。”忽喃喃道:“难怪有几处我总觉不自然,难以自圆其说。‘古木鸢’的目的,若是引出背后的阴谋家,那一切都说得通了。”
耿照犹豫片刻,终于还是鼓起勇气,握拳道:“追捕‘古木鸢’之前,能否让属下先与他见一面?我……有些事想当面问清楚。”
慕容柔回过神。
“你这便要收网了?背后的阴谋家是谁,意欲何为,有哪些党羽,都弄清楚了么?拿下古木鸢后,你自己能不能对付得了阴谋家?你要用什么罪名收缴古木鸢,证据又在哪里?”见耿照哑口无言,挥手道:“你自然要去见见古木鸢。把敌人的来龙去脉,全都弄清楚,回来向我禀报。他若问到你,你想怎么说便怎么说,只用不着提到我。”
“若他问起了将军──”这也非不可能之事。古木鸢要对付那灰袍客,情况之严峻,与耿照所面临者无分轩轾。若能拉上镇东将军,古木鸢未必不心动。对耿照来说,这是相当贵重的谈判筹码。
“他不会问。”慕容柔难得大笑起来。“你也太小看那人了!我若说得只字词组,反教他小瞧了我。你能活着走到他跟前,已足够说明许多事,毋须代我发言,做好你的本分罢。”顿了一顿,又道:“至于佛子的下落,须确实掌握,将他送交本镇发落。此人牵连许多秘密,落入有心人之手,是要出乱子的。”
耿照反复思索几日,也是这个意思。明姑娘虽是一片好心,此法却不能解决他与老胡的困难;他既不能对老胡交代,老胡也难以向母亲言说,与其一味逃避,不如直面相对。“属下会彻查佛子的下落,将他携回,将军放心。”
慕容柔点点头,良久,才转过身来。这是继堂上那图穷匕现的一霎间,两人视线再度交会,将军淡淡含笑,弯睫垂敛,低道:“这些日子,难为你了。回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