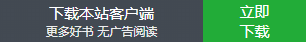强求不得
都是至亲,且统共就这几个人,晚饭的两桌席就都摆在了堂屋。
男人先坐,其中云意当仁不让地坐了男桌的首席。云意坐下后便叫成铭坐,成铭则推让谢尚,谢尚如何能肯?不免和成铭推让一回。
到底叫成铭坐了上首后,谢尚又和云敟云敩两个表兄弟告了罪后方才在下首坐下,云敟兄弟则打横做陪。
男桌的位次定了,女桌这边就简单了。
看着红枣跟着方氏、云敏坐下,郑氏招呼成功道:“功儿,快过来坐。”
至此一直只顾说话的方氏方想起两个孩子,笑道:“芮儿和功儿今儿倒是安静!”
云芮应道:“孙儿和功弟弟刚刚听奶奶讲家乡的事觉得颇为意思。真想尽快回家乡瞧瞧。”
云意隔桌听出了趣味,忍不住插口道:“芮儿,你刚都听到哪些家乡事了?”
云芮转身笑道:“爷爷,刚奶奶和姑姑、尚婶子还有娘谈论家乡的时水。”
“说每年春天的时候,就有人从远山拉这么粗,”云芮伸手比划:“怕是有三四寸粗的山毛竹进城来卖。毛竹买回去后剖开,刮干净里面,然后挂在檐头的滴水下接等雨水引入水缸。”
“屋顶留下来的雨水难免混有沙泥,但等存放一夜,这水就清崭崭的,好喝不说,洗衣也比咱们京城的玉泉水清亮干净,不掉色。”
“对了,据说咱们江州出产的天水碧,就是由这雨水调和颜料染就。是别处都没有的鲜绿。”
“不过最好的雨水还是时雨。黄梅时节天天下雨,几场大雨一下,屋顶冲洗得干干净净,接下来的雨水便不带一丝尘星儿,最为甘甜醇厚,泡茶煎药都好用。”
……
“爷爷,”云芮最后期待道道:“奶奶说咱们家乡老宅里有几十口缸,存放着全家一年用的时水。爷爷,年底咱们回乡,我就能喝到咱们家乡的时水茶了吧?”
看着大孙子眼里扑闪的星光,云意笑得合不拢口,连连点头道:“能,一定能。芮儿,爷爷告诉你,咱们江州的时水茶比这京里的玉泉水可是一点也不差。”
顾忌着女婿,云意就没说更好。
谢尚正在追儿子,眼见云芮伶俐,心里喜欢,笑赞道:“难为芮儿小小年岁竟知道这许多家乡事。”
傻爹云敟眼见儿子人前露脸,不免得意笑道:“芮儿虽生在京城,但到底还是江州人,如何能够忘本?”
“说句心里话,我也想咱们江州的时水茶了!”
……
成功听得艳羡,拉着他娘云敏的衣裳小声道:“娘,我也想去江州喝时水茶。”
云敏……
俗话说“衣锦好还乡”。江州远在千里之外,来回一趟,不说路费,只说家去后给本家各房的礼物,没得两三百两可不好看,而回来,家乡的风物土产必是也得给婆家亲戚捎些,如此又是一笔花销。
京官里成家算是颇有家资。但她公婆还在,没有分家,男人又只是个秀才,家常没甚进项。
现家中吃穿都是公中,人情往来则靠她和孩子的月例银子八两支撑——其中她月例四两,两个孩子各二两。
男人的月例二十两,只勉强够男人自己买书、买笔、买墨、郊游应酬,根本贴补不了她。
当然她手里嫁妆私房还是有些的。但这些是她一辈子的依靠,如何能轻易拿出?
何况她丈夫现在功名未就,现在回乡一来不够显赫,二来招她公婆抱怨不懂事,耽误男人念书,三则两个妯娌都不是省油的灯,趁她不在,不定会怎么挑灯拨火,蛊惑公婆。
看一眼含笑不语的男人,云敏抚慰眼巴巴的儿子:“功儿,明春化雪的时候,娘给你买毛竹存雪水,好不好?”
成功倒是不贪心,高兴应道:“好!”
方氏就在旁边,闻言不觉心疼——女儿嫁得远,想回趟家乡都不容易。
现自家在京做官还好,但等放了外任,想再见都难了。
下意识地看一眼红枣,方氏叹息:人拗不过命。
谢尚原是极好的女婿人选,谁知月老的红线却拴在这位身上?
往后反倒是要笼络好这位,如此即便自家放了外任,女儿孤身在京,遇事也不至于连个出头说话的人都没有。
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女儿外孙将来能有依靠,方氏瞬间对红枣热络起来。
看出红枣对她大孙子的喜欢,方氏立刻招呼大孙子道:“芮儿,你挨着你尚婶子坐。”
云芮求之不得,小跑到红枣身边殷勤道:“尚婶婶,我同你坐。”
红枣笑:“好!”
云芮眉清目秀,能说会道,正是红枣这个怪阿姨喜欢的小正太。
眼见横座空出不好看,方氏又道:“敟儿媳妇,敩儿媳妇,难得今儿尚儿媳妇也在,这布菜的事且交给丫头,你两个也坐下,大家好说话。”
于是郑氏和何氏也坐下了。
云家规矩大,媳妇在婆婆跟前一贯只有规矩,没有座。现方氏开口叫座,两个人都颇觉得脸,喜滋滋地坐下不提。
云敏素知她娘不待见红枣,但看她娘对红枣突然热情,微微一思索便就明白了她娘的苦心。
云敏心里感念,就不会让她娘唱独家戏。
在谢尚和红枣给云意方氏敬酒之后,云敏也举杯道:“尚弟妹,我嫁在京师,今夏你和尚兄弟圆房这样大的喜事也没能到场。现借花献佛贺你一杯,祝你和尚兄弟白头偕老,百年好合!”
成功跟着举起自己的蜜水杯道:“尚舅母,祝你和舅舅发昏大喜。”
成功到底还小,把新婚误说成了发昏。
红枣闻言一愣,转即噗嗤一声笑了出来——不是发昏她能无保留地和谢尚这样那样?
成功虽是口误,但却是真相了。
红枣今儿原就装扮得粉面桃腮,加上刚喝了两杯酒,有点上脸,当下这一笑仿若花开,看花了一屋人的眼睛。
云敟和谢尚碰杯道:“表弟,恭喜,恭喜!”
谢尚压根没问喜从何来,直接仰脖干了。
眼见谢尚喝得痛快,云敩成铭相继举杯。
云意笑呵呵地看着。
状元外甥不能成为自家女婿固然遗憾,但人各有命,强求不得。更犯不着耿耿。
何况敏儿的夫婿不差,只是不似外甥出挑而已!
大理寺的官做久了,云意于功名利禄反倒是看淡了。
宾主尽欢后,红枣坐上轿子,不自觉握拳砸了一下座椅。
这京城的破规矩,说什么文官出门必得坐轿。搞得她现在想和谢尚共乘说话都不行。
谢尚喝了酒,一个人坐轿子里也想倚媳妇肩头靠靠。
下回出门还是坐车,谢尚决定不管御史台的弹劾。
横竖御史台每年必有一弹。谢尚心说:他别处谨慎些也就罢了。
正是全京城女儿女婿各回各家的时候。
虽已入夜,街头巷口却塞满了车马,红枣和谢尚的车队混在车流中走不上前,只能小步往前挪。
未曾行到一半路,谢尚一个人在轿子里就呆不住了。
趁轿夫们等路歇轿的功夫,谢尚干脆地下了轿。
显荣看见刚要询问便见谢尚摆了摆手,撩袍往后面走去。
显荣下意识地闭嘴跟上。
堵车总是让人焦躁。
借着夜色掩护挑着轿帘看路况的红枣看到谢尚突然下轿不知何事,便一直注视着谢尚动作。
看到谢尚走过来揭开轿帘一角,红枣以为他有话说便倾身去听,不想谢尚一把握住她的手道:“红枣,咱们挤挤!”
不待答应,谢尚已然躬身蹿进轿子硬挤坐下。
红枣……
显荣……
轿夫……
“老爷,”反应过来红枣赶紧阻止:“这轿子乃是人抬。咱们两个人,轿夫们怕是抬不动。”
“怎么会?”谢尚搂着媳妇的腰不以为然道:“小轿不都是两个人抬?再说咱们两个身量都不胖,而且现在走走停停——这要是都抬不动,真可以换人了!”
对于谢尚的歪理,红枣不敢苟同。但看着已然歪到自己肩头上的脑袋,红枣到底没再提。
谢尚晚席喝了不少酒,现在酒劲上来,想必很不好受。
横竖现在路堵,轿夫们一时也走不了几步——实在不行,就轮班抬。
她且先顺着谢尚,但等他过了酒劲再说。
红枣拧开自己的保温杯盖后把杯子递给谢尚:“老爷还是赶紧喝口茶润润吧。即便高兴,今儿也不该喝那么多酒!”
“过节嘛!”
听出红枣语气里的关心,谢尚没有为自己多做辩白。他就着红枣的手汩汩地喝了几口,又把头挨蹭回红枣肩头撒娇道:“红枣,一个人坐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实在无趣。咱们下回出来还是坐车吧!”
红枣巴不得如此,但犹豫问道:“可以吗?”
“有什么不行?”谢尚反问:“轿帘拉上,谁知道里面坐得是谁?”
这话一听就觉得不妥,有钻规章空子的嫌疑。但看着跟牛皮糖一般扭在自己身上的谢尚,红枣实在无法效仿拒与君王共乘的先贤班昭撂下脸来跟谢尚说道理。
谢尚今晚喝多了,红枣温柔地想:说什么都做不得数。
她只要顺着他说就好。
……
跟过来的显荣看到谢尚所为不觉抽了抽嘴角,心说:至于吗?这才分开多久?
他们老爷这股子黏糊劲儿,也是没谁了!
长此以往,必将夫纲难振。
不管私心里如何吐槽,表面上显荣却是风轻云淡,似乎谢尚刚刚的蹿轿是世间最寻常不过的事,不足惊怪。
轿夫们看显荣淡定,便也跟着淡定——虽说接下来要抬两个人,但如老爷所言,街面上二人小轿都是两人抬一人。
而他们能从万千庄仆中脱颖而出被选为轿夫,气力原就异于常人——可抬着轿子奔跑。
何况家去就几里路,且已经走了一半。
海量岛国“动作大片”精彩视频免费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