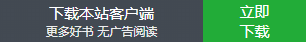第76章 鸿门
第76章
论起“骗人”,谁也比不过宁殷当初装乖卖巧,为了能留在虞府无所不用其极。
虞灵犀心知肚明。
可听到那句“对我坏点没关系”,心尖还是止不住一颤。
“第一个骗我的人,已经死了,死得好难看。”
宁殷像是想起了遥远的过去,嗓音也变得轻淡起来,“不过若灵犀骗我,我却是舍不得……只能关起来,将这条骗人的舌头一点点吮破咬碎,直至灵犀说不出话,只能呜呜咽咽哭着求饶。”
他抬指按了按虞灵犀的唇瓣,眼底晕开一抹墨色,绮丽而又痴缠。
宁殷此时定是心情很好,连呼出的气息里,都带着轻松的笑意。
可虞灵犀却笑不出来。
心中像是塞着一团棉花,心事隐隐沉闷。
她知道,如果自己想要宁殷的心,这个小疯子定然也会毫不迟疑地挖出来擦擦干净,然后再笑着送给她。
可对于虞灵犀捧出的真心,他却始终保持一定戒心。
好像在他的潜意识里,压根不会有人会将真心交予他。
第一个骗宁殷的人是谁?
她不可抑制地揣测:宁殷如此谨慎凉薄,是拜那人所赐吗?
“不会骗你。”
虞灵犀轻声喟叹,顺势依靠在他怀中。
对于心思坦荡的人来说,说两句真心话并不是难事。
于是,她细嫩的手掌轻轻拢住宁殷的指节,引着他的手贴在自己心口,让他感受那一刻澎湃的心跳。
“不信你摸摸。”
虞灵犀微微侧首,轻声道,“我的心跳不会说谎。”
宁殷不说话了,下颌埋在她的肩窝,感受着掌心下柔软的轮廓。
半晌,他意味深长道:“摸不出。”
“嗯?”虞灵犀不解。
宁殷垂眸,于她耳畔道:“衣裳太厚,碍事。”
“……”
虞灵犀反应过来,倏地瞪大眼,将他的手甩开。
宁殷却轻松按住她的腕子,欺身而上,指节顺着她的手腕往上,撩过颈侧,轻轻捏住她的下颌固定。
他迫使她望着自己,直至她脸颊泛起了绯红的热度,方笑着俯身,牙尖咬住她的下唇。
托在后颈的手掌稍一用力,虞灵犀便惊呼一声。
殊不知门户大开,便被蓄谋已久的人趁虚而入。
等到马车停在王府门前,虞灵犀已是面红耳赤,目光涣散,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
绝对不能骗小疯子,舌头真会被吃掉的。
与此同时,宫中。
皇后滚动手中串珠,问:“静王当街抢走了退婚的虞灵犀?”
“众目睽睽,千真万确。”
崔暗慢吞吞拖着语调道,“先前几次暗杀皆以失败告终,咱们的人折损严重,静王若再娶了虞家的女儿染指兵权,形势必定对娘娘和小殿下大为不利。”
皇后虚着眼,不答反问:“崔暗,你一心为本宫和废太子出谋献计,到底图什么?”
崔暗敛了眼底的暗色,跪拜道:“自然是感恩娘娘大德,结草衔环以报。”
“行了,这话你哄哄别人也罢,骗不了本宫。”
皇后拔下金钗挑了挑佛龛前的烛火,半晌道:“本宫记得,薛嵩贬去了光禄寺?”
崔暗稍一思索,忙道:“臣这就下去安排。”
“静王狡猾,给出的诱饵要足够大,才能引他上钩。”
皇后将金钗插回发髻间,声音平静得仿佛不是殊死一搏,“去吧。再失败,你便不必来找本宫了。”
这次,她要亲手了结这小畜生。
就像当年,了结他娘一样。
……
因是除夕新年,这几日,虞灵犀都老老实实呆在虞府中,陪伴爹娘兄姊。
嫂嫂苏莞有了两个月的身孕,添丁之喜,府中的除夕夜便比往昔更为热闹。
庭中明灯如昼,天边烟火灿然,虞灵犀忍不住想起去年此时,宁殷一边饮着加了重辣的屠苏酒,一边红着薄唇说“小姐是这世上,待我最好的人”的模样……
嘴角不禁扬起一抹浅笑,不知宁殷今年在静王府会怎样过年。
大概连一副对联、一盏热闹的红灯笼都不会有吧,偌大的府邸,他总是孤零零活在坟冢里一样。
想着想着,虞灵犀嘴角的浅笑又淡了下来,抬手摸了摸髻上夹血丝的瑞云白玉簪,化作一声轻叹。
守岁过后,虞灵犀沐浴更衣,打着哈欠往寝房走。
内间的垂帘已经放下,侍婢提前整理好了床榻被褥,虞灵犀未加多想,撩开帐帘坐了下去。
却冷不防坐进一个又热又硬的怀抱中,不由吓得三魂去了两魂。
惊叫声还未喊出,嘴已经被人从后捂上。
宁殷将她牢牢按在怀中,带笑的声音从耳廓传来:“噤声,将人引来了本王可不负责。”
虞灵犀惊愕,半晌才放软身子,拉下他的手掌回身道:“你怎么在这?”
“去抄家,路过此处故地重游,想起了灵犀。”
宁殷轻轻掰过虞灵犀的脸,墨色的眼中有未散的霜寒,轻慢笑道,“所以来看看。”
大过年的去抄家?
明明是炙手可热的静王殿下,怎么活得比以前的卫七还要岑寂孤寒?
虞灵犀张了张嘴,千言万语,最终只化作一句:“你有压祟钱不曾?”
宁殷眼尾微挑,似乎在问“那是什么东西”。
虞灵犀便垂首,从自己刚得的钱袋中摸出两枚铜钱,用红纸包好,塞入宁殷的手中。
“别嫌钱少,左右图个吉利而已,你也不缺银子。”
虞灵犀解释,“这是压祟钱,睡觉时放在枕头下,能保整年顺遂平安。”
帐帘昏暗,宁殷难得流露出几分新奇来,摆弄着掌心红纸包裹的两枚铜钱道:“压什么祟?”
虞灵犀寻了个舒服的姿势,与他并排倚着,小声回答:“自然是压恶鬼邪祟。”
宁殷笑了声:“本王不就是这世间,最大的恶鬼邪祟吗?”
虞灵犀眨了眨眼。
这话……似乎也不无不对?
“依本王看,不如是‘压岁’。”
宁殷虚握五指,将两枚铜钱握在掌心,凑上前压低嗓音,“岁岁的岁。”
说罢,他揽着虞灵犀的腰身形一转,自上而下禁锢着她。
名副其实的“压岁”。
翻身时衣袍带起疾风,撩起了帐帘如波澜鼓动,宁殷的眉目轮廓变得格外模糊深邃,唯有一双漆眸有着摄魂夺魄的蛊惑。
奇怪,虞灵犀竟然会觉得宁殷的眼神蛊惑。
明明他是个五感缺失,定力强到近乎自虐的人。
“小姐,汤媪备好了,您等被褥暖和了再睡。”
胡桃抱着一个用绸布包裹好的铜汤壶进屋,脆声道。
虞灵犀一惊,下意识撩起被褥一盖,将宁殷推到榻里藏好,道:“你放在案几上!”
声音有些焦急,胡桃吓了一跳:“小姐?”
宁殷眯了眯眼,抬手捏了捏她的腰窝。
虞灵犀“唔”了声,心脏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
她忙咬唇瞪着始作俑者,胡乱编造道:“我在脱衣裳呢,你别过来。”
好在胡桃并未起疑,将热乎乎的汤媪搁在案几上,便掩门退出去了。
虞灵犀竖着耳朵,直到胡桃的脚步声暂且远去,这才长舒一口气。
“不是脱衣裳么?脱。”
宁殷侧身曲肘,以手撑着脑袋,被褥中的另一只手往下,舔了舔牙尖笑道,“想盖章了。”
……
烟花的热闹到近乎天亮时才消停。
虞灵犀不知宁殷何时走的,醒来时身侧已没有那人的温度。
若不是旁人瞧不见的地方还落着一枚深红的“印章”,她险些会以为昨晚的短暂相见是一场梦境。
梦醒空荡,却又像品了一颗糖,回味余长。
好在很快是上元节,灯会夜游,官民同乐。
那晚戌时,天子会率王孙贵胄登上宣德门,观高台灯市,接受万民朝拜。
但因皇帝尚在长阳宫养病,此次登楼,便推举七皇子宁殷代劳。
按理说,宁殷对这种场合毫无兴致,应是不会露面的。
但大家都在猜测,能有资格代替天子行礼的人,极有可能会成为皇位的继承人,七皇子但凡有点野心,都不可能拒绝这项殊荣。
所以,宁殷是想做太子么?
虞灵犀不清楚。
戌时,虞灵犀身着红妆礼衣,提着一盏琉璃灯,与虞辛夷一同登上宣德门西侧楼台——那里是后宫嫔妃和女眷观灯的场所。
而宁殷和宁子濯等皇子王孙,则代替天子站在东侧楼台之上。
极目望去,夜空深沉,宫门下人声鼎沸,千万盏花灯化作光河蜿蜒。
虞灵犀手搭在宫楼的扶栏上,远远注视着东侧缓步上楼的宁殷,紫袍玉带,冷俊无双。
嘴角忍不住上扬,却见一旁的虞辛夷走上前,伸手打断她的目光道:“可要阿姐借你令牌,过去找他?”
虞灵犀这才收回目光,不好意思地笑笑:“不必啦。”
她约了宁殷燃灯会结束后,一起去市坊赏灯猜谜。
今夜上元,不受礼教束缚,可以通宵达旦地赏灯游玩呢。
风一吹,满街的花灯摇晃,如星子散落人间。
薛岑站在拥挤的人群中,一眼就瞧见了宫楼之上的虞灵犀。
那么多衣着华丽的贵女、命妇,唯有虞灵犀如出水芙蓉般美丽亮眼,额间一点嫣红的花钿灼然绽放,映得满楼灯火黯然失色。
她的眼眸依旧漂亮温柔,只是,再也不会望向自己。
薛岑是跟着阿兄来此的。
废太子死了,祖父也卸职归家,与虞家的婚事告吹沦为全京城的笑柄,薛府陷入前所未有的颓势之中。
薛岑偶尔彻夜不眠,会听到三更半夜阿兄匆匆出门的声音。
整座薛府,唯一没受打压影响的,似乎就是薛嵩。
渐渐的,薛岑起了疑。
薛家扶植的废太子已经死了,他不知道兄长还在为谁奔波劳累……亦或是,他暗中侍奉的,压根不是废太子?
心中疑窦重重,薛岑跟着阿兄的马车来到宫门下。
人跟丢了,他看见了宫楼之上浅笑嫣然的虞灵犀。
像是扑火的飞蛾,心中灼痛,却又情不自禁吸引。
光禄寺和礼部的吏员领着一班杂耍艺人和商贩上楼,人群拥挤起来,薛岑被后面的稚童撞得一个趔趄,再抬首时,楼上已没有了虞灵犀的身影。
他微红的眼眸黯淡下来,逆着人群,孤零零地往回走。
火光直喷三尺多高,惹来西楼的女眷们欢呼叫好。
是礼部甄选出来的民间杂耍班子在给宁殷献艺,寓意“与民同乐”。
宫墙上风大,虞灵犀对瓦肆杂技没有兴趣,便换了个避风的地方呆着,只想燃灯会快些结束,好和宁殷一同去市坊夜游。
“哇!这火喷得好高啊!”
一名十四五岁的少女挽着妇人的胳膊,兴高采烈道,“阿姊快看!都快喷到静王殿下的脸上去了!”
“嘘!静王殿下的名号,岂是你能大呼小叫的?”
妇人明显顾忌许多,压低声音解释道,“这杂耍班子来自漠北,能歌善舞,通晓百戏,自然不是汉人能比的。”
听到“漠北”二字,正在饮酒暖身的虞灵犀一顿。
她起身,闻声找到那名妇人,福了一礼道:“夫人方才说,这支献艺的杂耍班子,是哪里人?”
妇人想必也是官宦人家的命妇,立刻回了一礼,答道:“是漠北人。奴也是曾听夫君说过,他们都是先帝灭漠北后掳来的奴隶,在京中瓦肆很有名。”
虞灵犀趴在栏杆上极目远眺,那个正在朝着宁殷方向喷火表演的汉子越看越眼熟。
漠北人,上元节,鸿门宴……
心脏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狠狠攥住,虞灵犀手中的琉璃灯吧嗒坠落在地,四分五裂。
她后退一步,转身就走。
提前了一年!
如果没猜错,因为这辈子虞家并未覆灭,导致皇后残党忌惮宁殷势力,联合宦官精心准备的那场血腥鸿门宴,比前世记忆中的时间提前了整整一年!
即便是前世震慑天下的摄政王,亦是在这场刺杀中身负重伤,事后才以烧活人为灯泄愤,更遑论……
现在的宁殷还不是摄政王啊!
“阿姐!”
虞灵犀一把拉住正在安排百骑司巡逻的虞辛夷,抖着嗓子道,“令牌借我一下!”
“怎么了,岁
岁?”
虞辛夷一头雾水,“你的脸色怎么……”
“献艺的杂耍班子是漠北刺客,皇后设燃灯宴,联合宦官要刺杀静王。阿姐,快禀告兄长救人!”
来不及解释更多,宁殷虞灵犀解下虞辛夷腰间的令牌,挤开人群朝东楼大殿方向不要命地奔去。
直到妹妹的身影消失在攒动的人群中,虞辛夷才反应过来,召集下属道:“杂耍班子有问题,速报禁军!”
轰——
三丈多高的灯楼拔地而起,城门亮如白昼,百姓欢呼若海。
鼎沸的人声涌来,将虞灵犀的呼喊声淹没。
“宫墙东侧乃皇子王孙之所,女眷不可擅闯!”
禁军交叉长戟,拦住了气喘吁吁奔来的虞灵犀。
“我奉虞司使之命,有要事禀告静王!”
虞灵犀拿出了阿姐的腰牌。
禁军依旧拦在路口,虞灵犀索性一把扯下腰间的龙纹玉佩,“见此玉者,如静王亲临,你们谁敢阻拦!”
龙纹玉佩是皇子专有,禁军果然被唬住了。
虞灵犀不再耽搁,趁着禁军迟疑的当口朝正在观灯的宴席走去。
楼上殿门大开,见到一位红妆美人气喘吁吁地闯进来,一时间宴席上众人皆有些惊讶。
“这不是虞二姑娘吗?”
“她来作甚?”
宁殷放下了手中的杯盏,极轻地一声响,四周细微的议论声立即戛然而止。
虞灵犀的视线与宁殷对上,定了定神,迈步越过那群杂耍的艺人,朝宁殷走去。
“殿下的玉佩落下了,臣女为殿下送来。”
虞灵犀竭力稳住呼吸,跪坐在宁殷面前,双手递上那枚玉佩。
她朝着杂耍艺人和某些大臣的方向使了个眼神,焦急之情全在不言之中。
察觉到气氛不对,宁殷的眸子便缓缓眯了起来。
他神色如常,甚至带着优雅的笑意,低声道:“你不该来的,岁岁。”
继而他一手抓住虞灵犀的腕子拽入怀中,一手抬起空着的杯盏遮挡!
几乎同时,一把细长的匕首刺穿杯盏底部,森寒的光映亮了宁殷幽暗的眸。
震地巨响,灯楼上的齿轮开始转动。
火花四溅,宛若金银碎屑点缀夜空,一片火树银花,百姓的欢呼声如浪潮拍来,盖住了殿楼上的动静。
事出紧急,虞焕臣能调动的人不多,很快被崔暗的人拦在了城楼之下。
两军对峙,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崔提督这次真是将老本都搬出来了。”
虞焕臣按着腰间的刀刃,一袭银铠白袍随风猎猎,“你和漠北有勾结?”
闻言,崔暗慢吞吞道:“来的不是虞将军,真是可惜。不过无碍,父债子偿也是一样。”
“什么意思?”
虞焕臣皱起了眉,按在刀柄上的手指不着痕迹地点了点。
藏在暗处的虞辛夷立刻会意,隐入人群之中。
“虞将军见过本督许多次,可每一次,他都没想起我是谁。”
崔暗笑得阴沉,“他好像忘了那些被他杀死异族人,忘了那一串被草绳镣铐串连着、赤脚跌跌撞撞送入京城的漠北俘虏中,那个瑟瑟发抖的小少年。”
偷吃小姨子视频漏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