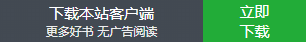第129章 番外(一)
(1)孽债
春夏交替时是一阵阵连绵细雨,春日的勃勃生机被洗涤得碧绿瓦亮,茶坊外一枝杏花很懂生存,斜探入窗,避免了初绽的花瓣被风吹雨打。
但雨声闷沉,很是扰人清静。
姬玉落的小几靠着窗,她翻着南边来的密信,信上多是催雪楼中明里暗里的波动,江湖帮派就像个小朝廷,总少不得勾心斗角,从前有谢宿白坐镇,姬玉落尚能胡作非为明着出手,如今却不行了。
傲枝从宫里来,跪坐在一旁替谢宿白传话。
她尽心尽力说了许多。
但谢宿白是个话少的人,这些断不全出自他之口,他约莫只给了两三句话,傲枝最会揣摩上意,总能将谢宿白的话掰开揉碎。
“便是王朝更替,也免不了动荡局势,人多的地方总有纷争,催雪楼也不可例外。如今换了主子,小姐又这样年轻,从前皇上多有庇护,那些庇护多少在旁人眼里生了嫉恨,就像是周白虎,可也不是人人都像周白虎那样直性子,坏心思写在脸上,藏在暗地里的才要当心。”
“可也不能一味斩杀,只怕寒了人心,令局势失衡,主上知小姐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之人,可也要懂得制衡才好。”
“主上余威虽在,可压得了一时压不了一世,往后小姐要学着保全自己才是。”
说到这里,傲枝顿了一下,“好在如今有霍大人在,有人护着小姐……”
这恐怕也是皇上费心救霍显的缘故。
看着姬玉落那半边无暇的侧脸,傲枝总觉得心里堵得慌,自幼的悉心照料和教导,就像是给旁人作了嫁衣,偏那一腔情谊,还不得让人知晓。
唉,傲枝深吸一口气,只能岔开心思。
窗外风大了,吹得雨往里飘。
姬玉落要关窗,那杏花偏是阻碍,她没有什么怜香惜玉的心思,手里还翻着密信,头也不抬,无情地将花儿推出窗外,“砰”地一声,紧了窗子。
雨声小了。
傲枝言尽,才问:“小姐何时离京?”
姬玉落搁下信,说:“离京之前,我会进宫拜谢皇上。”
她稍顿半息,又说:“他身子不好,又有朝政要忙,无需再为我费心,保重自身才最重要,药都在喝么?”
傲枝回了是,两人再无旁的话说,静了片刻,她也就辞别回宫去。
身影拐过屏扇,姬玉落张了张嘴,还是没把人叫住。
街边的雨小了,青石砖铺的地面平滑如镜,倒映着两侧林立的店肆。
雨天人少,回程的马车走得顺畅。
姬玉落歪在榻上,说:“绕道往东直门大街走。”
她虽然不再用锁链拘着霍显,可也没有准许他出门,只留了一方院子给他走动。
一来是因为他身体没好全,二来是因为如今京都盯着霍显的人太多了,个个都没藏着好心,总之姬玉落现在有后遗症,人还是在眼皮子底下看着比较好。
霍显秉着“人在屋檐下”的道理,也是出奇安分,近来看他常敞坐在石阶上雕木头,打发打发时间也好,姬玉落便打算去木雕店给他挑两块好木料。
但愿他能再安分几日,直至顺利离京。
只是拐过长街,却调转车头,避到一旁。
姬玉落推开车窗,就见一列身披麻戴孝的队伍自街巷走来,最前的汉子手提铜锣,却没有敲响,中间的男男女女也皆是无声抹泪。
显然是送丧,但送得悄无声息。
哭丧哭的比这雾蒙蒙的雨还要安静。
吸引姬玉落注意的,是站在前面的姬娴与,她身边就是姬云蔻。
姬云蔻哭得敷衍,她浑浑噩噩跟着,整个人看起来没什么精气神,恍如行尸走肉,姬娴与倒是哭得真诚,那双眼都肿成核桃仁了。
她沉浸在悲伤里,连脚下的石子都没有注意,左右一打滑,险些撞到姬云蔻。
姬云蔻也只慢吞吞瞥她一眼,努了努唇,却没有说话。
她知道,姬娴与哭得这么伤心,却未必是为了那位隐形人似的祖母。
江氏从早些年起就虔心礼佛不见客,姬娴与见她的次数亦是寥寥,人与人之间的情谊都是处出来的,若没了相处,那点看不见摸不着的血脉能值几分情呢,而今江氏病逝,她们这些孙辈,到底生不出多少真情实感的难过,可事情发生在如今,姬家江河日下的时刻,桩桩件件累起来,就让人甚感悲凉。
姬娴与哭,是在哭这世事无常的无措。
可姬云蔻的眼泪早在顾姨娘死时流干了,后面那几日,她又被将要出嫁的“长姐”吓得不轻,神智都飞走了大半,每日愣愣的,现在反而心无波澜。
反正,左不过也是更惨些罢了。
然她收回视线,却倏然惊心,瞳仁都瞪大了。
马车里的那方身影叫她双手都下意识打颤,仿佛见鬼一样,催得前边引路嬷嬷走得更快些。
姬府门外挂着白灯笼,两侧摆放的花圈是自家安置的,府里甚至没有宾客来吊唁。
若是还是从前,总不至于是这样的光景。
就国子监那些学生,就能把大门排成长龙。
可今时不同往日,林婵甚至在为无人上门而感到庆幸。
这些日子她受尽冷眼,嘲讽的话更是听了一箩筐,眼下即便有人来,怕也只是黄鼠狼给鸡拜年,还不如不来。姬府的好名声是毁尽了,这场丧事更不敢大肆操办,夫妻俩都恨不得能偷偷过礼,不要再让人注意到姬家才好。
于是林婵愈发敷衍,哭都不哭了,直坐到廊下去发愣。
愣着愣着,眼便红了,
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她曾经也是家里捧在手心的宝贝,一朝为人妇,竟再也没有顺心过。
所有的苦难,似乎都从她相中姬崇望开始。
那个年轻俊朗的穷书生,可如今再想,那天的日头太大,日光像是给姬崇望渡上一层美好而朦胧的假象,让她动了心,也生出执念。
年幼傲气的小姐啊,心心念念的就要占为己有,哪里管他是不是心有所属。
但这么多年,看多了姬崇望虚伪的皮囊,知晓他内里的狠毒自私,年少时的怦然心动早就偃旗息鼓了,多年经营,不过是为了人前最后一丝体面罢了。
可现在连体面也没了。
林婵拉住忙碌进出的姬娴与,麻布粗衣衬得她那么娇小,她受惊低呼:“母亲……”
林婵眼里迸出光,紧紧攥住姬娴与的手,说:“我听说你阿姐在御前侍奉,新帝温文尔雅,是个和善的人,她必定能说上话。你不是与她最好么,你去与她说说啊,姬家也是她的家,倘若姬家出事,她也捞不着好!”
“母亲……”姬娴与哭着将手抽出来,她带着哭腔说:“这里早不是阿姐的家了,我们都对不住她,又怎好求她。您与父亲犯下了天大的错,往后我们若留着命,就好好赎罪吧。”
林婵不依不饶,却逢姬崇望经过,他淡淡道:“为难孩子做什么,求谁都无用,新帝不会留我。”
到底是在官场周旋了二十年的人,朝堂局势,他比谁都看得明白。
便是没有姬玉落这桩事,当初他利用国子监造势,助新帝登基,单是这一件,就注定了他迟早要沦为不能说话的弃子。
他的存在,便是新帝的眼中钉,新帝怎么可能放任他继续在京都任事。
想必不过几日,调令就要下来了。
姬家的荣誉,竟只留了半辈子不到。
姬崇望面色沉静,可心中的哀凄不比林婵少,筹谋了那么多,赔上了那么多,到头来全是无用功。
然而,他到底是低估了新帝的仁慈。
丧礼不过一日,禁中的诏书便下来了,果然是辞了他国子监的官职,下放到地方任吏员。
连降数职,又是偏远地区,姬崇望却懒得为自己辩驳争取,他垂首不语的样子,像极了认命。
出城当日,经由城门之地,姬玉落马车帘牖敞开,露出张脸,安静地望着他。
说不上欢喜,也没有恨意,那稍稍挑起的眼尾,添的是漫不经心的嘲弄。
这种嘲弄,姬崇望曾经在一个孩子脸上看到过。
那日寒意涔涔,霜雪覆腊梅。
八岁的丫头由嬷嬷引着,打几簇梅花枝头旁绕过来,低垂的眉眼只盯着自己的鞋尖,那鞋面上已经破了个洞,但她抬起眼时脸上没有自苦的神情。
安安静静,黑白分明的瞳仁里也没有惊慌失措,冷静得不像是个八岁大的孩子。
那时,她只犹疑地唤了声:“父亲?”
姬崇望便知道,这是孽债,是尤黛月对他的报复。
后来送她出城当日,姬崇望站在角门檐下,那孩子透过车窗看他,神情便如此时,静得像口摸不到底的深渊,无波无澜,眼尾和唇角那点微不可查的弧度却恰到好处,仿佛一眼就能将你看穿、看透,还带着点懒得理你的不屑。
姬崇望从未与人说过,后来多次午夜梦回,他常常是一身冷汗惊醒。
他梦到那双眼睛,就那样笔直地望着他,望穿他!
他停在那里,姬娴与催促道:“父亲?该走了。”
姬崇望将包袱给她,只让她先去城门口排着长队,自己则径直朝对面的马车走来。
步履沉重,面色亦凝重。
车窗里女子支颐斜倚,浑身透着慵懒凉薄的意味,见他来,也不曾坐直,只是挑高了眼。
四目相对,周遭人群嘈杂,更显两相死寂。
姬崇望酝酿许久,道:“终究是她赢了,她恨极了我,你替她了了心愿,也算是交代。”
闻言,姬玉落先是挑了下眉,而后垂眼,很轻地笑了声,满是讥讽。
时至今日,她其实从未针对姬府做过什么,只是他自己运气不好,挡在了权利更迭的风口浪尖,这能怪的了谁呢。
而姬崇望却以为,姬家落到这个地步是她刻意为之,是在为尤黛月报仇。
……但她确实无意之中全了尤黛月的心愿。
思及此,姬玉落脸上的笑意渐渐收敛,神态稍显落寞和茫然,但只一瞬,便被车外一阵高音打破。
木雕店掌柜的捧来一块沉甸甸的紫檀木,展颜道:“姑娘您看,这便是小店新得的木料,您上回嘱咐过,小的便一直给您留着呐。”
姬玉落摸了摸那方木头,心里那点道不清的烦闷忽然消散,“回去吧。”
(2)浮木
雨夜雷鸣,天边乍闪过冷光。
姬玉落蓦地睁开眼,气息起伏不定,但人躺得板板正正,没有发出丁点噩梦惊醒的声响,然身边人似有所察觉,一只大掌压在她腰腹,将她整个挪了过来。
男人嗓音带着将醒未醒的腔调,说:“怎么?”
姬玉落侧头去看他,借着窗外银白月色,恰能见他深邃的眼窝和高挺的鼻梁。
她抬手摸准他唇上,指腹感受了下柔软温热的温度,心才堪堪定下来。
不及霍显再问,她就仰起脖颈亲过去。
那一下力道极大,撞得霍显困意全散。
乱七八糟的啃噬似是在发泄情绪,霍显启初还算配合,张开嘴予取予夺,直到那只揪住衣领的手不很安分地往下,直勾住裤腰,他才出手摁住她。
姬玉落挣了挣没挣开,恼得在他唇上咬了下。
霍显用手肘撑床,稍稍将自己支起来些,俯身用舌描摹她的唇形,逐渐掌握主动权。
打蛇打七寸,他动作娴熟地摸到姬玉落后颈,就着这一小块颈骨慢慢揉捏起来,仿佛开关一样,指腹上下摩挲间,怀里的人方慢慢冷静下来。
她动也不动,食指虚虚搭在他肩背上,任他一下、又一下啄吻餂舐。
许久,霍显松开她。
呼吸交缠,各自平复着。
他没有多问,只低眉看她。
姬玉落这个人心思藏得很深,便是枕边人,她也不见得会把想法一五一十剖析在你面前。
若非她自己想说,再怎么问也是无用功。
霍显抚着她的脊骨,心想她方才回来时比往日沉闷,屏溪说她在路上遇到了姬崇望……
像是能悉知他心里所想,姬玉落道:“不是因为姬崇望。”
她停了停,才说:“我梦到尤黛月了。”
霍显“嗯”了声,动作很轻地撇开她脸上的发丝,像是怕惊扰了她,“梦到她什么了?”
“她抱住我。”
“说要谢我。”
姬玉落皱了下眉,说:“她有病,她是个疯子。”
霍显“嗯”了声,没说话,等她说。
姬玉落也沉默好久,她盯着飘忽的幔帐,忽然冷情直白道:“她是个靠仇恨存活世间的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其实只是个窝囊废,想死又不敢死,只能假借报仇支撑自己,以便心安理得苟活而已。”
幼时姬玉落曾问她,活着如此没意思,为何要活着
那时尤黛月已是临终卧榻,遗言也尽数交代完毕,没什么可隐瞒了,只了无生趣地说:“你那混账父亲没死,我如何甘愿去死?”
姬玉落便冷嘲热讽道:“那何不杀了他一起死?”
这话仿佛触了尤黛月的逆鳞,她拖着孱弱病躯从床上爬起来,掐着女孩的脖颈怒吼:“你知道什么,你能知道什么!你和你父亲一样,养不熟的东西!”
姬玉落道:“我厌极了她贪生怕死又疯癫虚伪的样子,可我和她,好像也没什么不同。姬崇望于尤黛月,正如赵庸于我,他活着承载尤黛月的恨意,死了便会抽干她的生机。”
她说话时压了下眉梢,神色呈现出片刻的茫然,而后又冷静地轻叹:“当年乔循舍命救我,我丢下他跑了……霍显,其实我根本没那么爱乔家人。”
说罢,她停了停。
这样直白的剖析,她在告知他,她是个很坏很坏的人,却没有等来这个好人的评述。
真奇怪,她还真想听他说点什么。
于是姬玉落抬头看他,“你不说点什么?”
霍显却只垂目看她,唇线笔直,神色似很严肃。
乔家只是一个由头,一个让她去杀人报仇的借口,以便她能从浑浑噩噩中挣脱出来,披上有血有肉的皮囊,像个稍稍正常些的人游走世间。
因为她不想死,可活着又很没意思。
世人活着,本就需要很多寄托,很多盼头。
了无牵挂的人,才是最难活着的人,没有羁绊,生死便在一念之间,当那些杀害乔家的人一个个死在她手里,杀尽最后一人时,大仇得报,执念陡地消散,她便也没了生机。
是故自东乡县之后,她比往日更加沉闷。
霍显曾经以为,姬玉落是石缝里的坚韧不拔的野花,想是没有谁都能好好活着,实则恰恰相反。
从前靠恨支撑,往后靠爱支撑。
总得给她一样,才能让她过好半生。
而她数次把霍显从悬崖边上拉回来,如此费尽心机,也不过是在自救而已,他便是那海上的浮木,她需得死死抓住方能周全自身。
然他轻而易举把自己送到了敌人的刀刃下,断的实则是姬玉落的生路。
所以她拘着他,囚着他,不是在与他置气,是他可能……
吓着她了。
而他自负聪明,竟然现在才洞悉一切。
姬玉落见他发怔,伸手在他眼前晃。
霍显捉了她的手摁在榻上,看着她,喉头都有些干涩。黑夜中深吸一口气,平复了心绪,偎着她短叹说:“说什么,说你薄情寡义,丧尽天良?”
紧接着,他又很轻地呢喃一句:“可那能怎么办呢……”
姬玉落正想听听他要怎么办,撑在上面的人却忽然压了下来,姬玉落还在与他说话,没料他突然靠近,免不得愣了愣,“怎么?”
霍显看她一眼,俯身亲了下她的唇,道:“你不是说我是好人么,好人来度化你。”
姬玉落顿时失笑,“这有用?”
霍显道:“度化么,长此以往才有用。所以,玉落小姐,你什么时候带我走?”
闻言,姬玉落稍顿了一下。
如今霍显在京都其实是个很尴尬的存在,说他黑的有,说他白的也有,总之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他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洗白”。
但宣平侯府已经不管不顾,那宣平侯成日为这事与同僚争吵,从路上吵到太和殿,他那张被霍显磨练出来的三寸不烂之舌,简直颇有当初霍显舌战群臣的风范,眼下谁还不知道,宣平侯大有将霍显挪回霍府疗养的意思。
这个儿子,他是想要的。
而对此,霍显未置一词。
姬玉落本苦恼他或许想回去霍府,是以她看到宣平侯才会那般如临大敌。
她迟疑问:“你不想回霍家?”
霍显笑了下,“还是得回去一趟,改日你陪我一起去。”
四目相对,姬玉落眨了眨眼,悬了几日的心总算落回肚子里,然她面上不显,若无其事地“嗯”了声,甚至忘了惊醒自己的梦魇,那些或都不重要了,她说:“睡吧。”
霍显看她,鼻腔里溢出声笑。
他倾身过去,指腹摁在她颤动的眼睫上,姬玉落立刻就睁开眼了,问他做什么。
霍显掀开她的小衣,一本正经道:“做法,驱邪,以免噩梦缠身。”
嫩嫩高中生大胆啪啪视频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