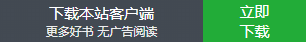第三百九十五章 血色海洋
颜奇率三百余人,已经至海盗军阵的前列,在前方有十余个千人多的阵列,由于被箭雨覆盖,已经混乱不堪。
颜奇并不畏惧,他的战甲是精光四射的铁甲,并且有铁盔和盾牌,根本不畏惧魏人的弓箭。眼前战场的情形,倒是令他暴燥和愤怒。魏人军阵凌迫而来,并用弓箭杀伤海盗,这给颜奇一种感觉,眼前的魏军根本未曾将他放在眼里,也未曾将数倍之敌的海盗们放在眼里。这种感觉,令纵横七海多年,杀人无数的颜奇感觉颜面尽失,他内心嗜血的欲望战胜了些微的胆怯和犹豫,无论如何,海盗军阵厚集,两翼已经向魏军的左右两侧更前方包过去,魏军射手开始专注平射那些包围到侧翼的海盗,但弓手人数少,两侧的海盗各有好几千人,一轮杀伤可能就几十人,威胁并不算大。
在颜奇张着凶目观察的时候,有个精瘦的海盗跑过来,半跪在颜奇面前道:“我家大王询问颜大王,是否顿步与敌中路僵持,右翼将士助守中路,左翼大军斜插敌后,成两面包围之状来打?”
中路突破,左路防骑兵,这是事前定好的方略,很明显是刘旦看到中路有些混乱,是以担心中路会顶不住压力,更不要说向前突击,因此刘旦有些担忧,便提出中路以防为主,待左翼兜过去,两边合力,包围抄掠,这样更容易获得全胜。
“和他说,不要再来烦我。”颜奇脸上满是暴戾之色,眼中也布满血丝,他对刘旦派的人说道:“正面破敌,叫他防好骑兵突袭。”
“是,小人即刻去。”
来送信的是刘旦的心腹,但这心腹也不敢保证颜奇会不会一怒之下斩杀自己。据说颜奇在晚间饮酒时除了仆役,侍女和歌妓外,尚要侍卫保护,这些人被挑中之后都会与家人决别,因为颜奇每饮醉必杀人,却是不一定杀谁,有时杀姬妾,有时杀仆役,有时也会杀侍卫。
这样的暴戾残杀之主,谁能不惧,刘旦派来的人,几乎是屁滚尿流的离开。
两军锋线在此时终于聚集到一处,海盗们在犹豫,对方的锋尖人数不多,没有想象中刀矛长矟相交的场面,而海盗的阵列是几百上千人混在一处,前排倒是全部以刀矛长斧为主,后排则什么样的兵器均有,每阵之间相隔几步或十几步,众人在此时互相踩踏拥挤,不愿主动向前,几千双脚在地面踩来踏去,将鲜血踩入泥土,尘土踩踏飘扬,整个战场都弥漫在黄雾之中。
而在群盗身后二里多外是众多的建巩物形成的码头,大海平静如旧,蔚蓝的海水在正午的阳光下散发着光泽,整个大海犹如蓝色的玉石,清澈,透明,而充满着平和之感。在不远处陆地上的人们,却是在做着殊死的搏杀。
在最后时刻,所有的锋锐之士没有丝毫畏怯和犹豫,卢文洛是第一批冲入前方的将士之一,与他冲锋敌阵时的时间相同,不同的小型的三角锋线几乎是同一时期一起冲杀了进去。
所有的锐士俱是持盾荡开前方的群盗,长对方的长矛铁枪长刀都荡开去,然后呐喊发声,将横刀劈斩过去。
被荡开防线的群盗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前,虽然魏军摆出了攻击的阵列,但是他们也是真的没有想到,眼前的魏军居然就真的没有迟疑,没有反顾,没有停滞,虽然脚步略缓,看来也是要等候阵列更加齐整,待所有魏军将士调整好步伐之后,当先之甲士,以一往无前,奋不顾身之姿,悍然就荡入了诸盗阵中!
鲜血喷晒了卢文洛一脸,他的横刀下劈,斩中了一个海盗的脸庞,直接将对方整张脸都劈斩了开来。
在惨嚎声中,那个海盗倒了下去,另外几支枪矛同时刺向上卢文洛,他的身形却极为灵动,脚步移动,同时继续用盾牌格挡,用多层牛皮和鹿皮蒙住,用精工打造的盾牌防护力不在铁甲之下,但正面被戳刺多下,还是会有被刺破的风险,所以卢文洛并不是将盾牌死死挡住,而是不停的挥荡。
相对南洋群盗,卢文洛可谓身形长大,他肩膀宽阔,腰身却很细,大腿粗实而小腿又稍细,这是长期锻体练力,又每天长跑锻炼出来的身形,在突入海盗群中的时候,他的刀盾不停的转动,不停的杀伤敌人,同时尽量护住自己,不使自己被如林般的刀矛所伤。
在卢文洛破开一个小口子的同时,无数锋锐之士,包括不少府军中的百战老兵亦是同样如此,整个海盗中阵的阵线上,大大小小的阵列同时被南安府军的锋线所击穿了。
在卢文洛身后是三名长矟手,其后又是五人,七人,九人,十一人的矟手,大半的矟手都被集中到锋线上了,在侧翼的一些小阵列中,则安排着刀牌手和弓手,大半的刀牌手仍在锋线之前,少量的刀牌手被安排保护侧翼的弓手。
卢文洛等人打崩一点之后,迅速就有矟手跟随而上,南安侯府的训练向来是以长矟为核心。若防御,长矟手是阵列正中的活动堡垒,长矟阵在,则大阵安然无事,长矟不在,则阵势不复存。
而在进攻时,长矟手亦是锋线的真正主力,他们手持着三米多长的锋锐长矟,矟尖与长矛类似,但矟体稍长,两侧开刃,又有些类似长枪枪头,长矟以戳刺为主,也可以挥,抡,在类制的长矟之前,那些海盗所用的杂质武器,驳杂不堪,使用的方式亦与真正的军人用矟之法相差太远,在卢文洛等突前甲兵的身后,传来不停的惨叫声,矟尖起伏不停,不停的戳刺或抡挥杀伤敌人,更大的空隙被打开了。
副营官李朴是葛存忠的老部下,鼓山盗的老人之一,现在任第二营下的营副统制,其身量高大,身高超过魏尺的五尺八寸,也就是一米八五左右,在闽人中是罕见的高大身材,其满脸虬髯,并未戴铁面具,脸上已经喷满了血污,其身上甲叶,亦是挂着缕缕血肉,衣甲已经被鲜血染红。
其年在三十五六左右,为盗十多年,见多了生死搏杀,哪怕身边刀矛如林,他亦十分冷静,左手持盾,右手却是持着夹马棒,这种、马棒十分沉重,重达十二三斤,制式兵器却没有这般沉重的存在,而李朴单手挥动却是毫无困难,他头戴铁盔,身披多重铁甲,有时候有海盗挥刀斩来,他略让一让,任由对方的刀斩在铁甲之上,划出长长的火星,并不能破甲而入。而反手一棒打过去,却是能将任何对手的头颅打凹限进去,脑桨迸裂,吓的四周的人肝胆俱丧。
更多的精兵锐卒,带队的武官,俱是如锋线之前的甲兵一样,蜂拥而入,拼力杀伤敌人,由于战线锋锐,府军将士突前的速度极快,几乎无有海盗能是当面之敌。
秦东阳在第一营锐阵之前,他身后的甲兵都是一时之选,就算如此,诸将亦是将他放在稍微靠后的位置,不使这个统兵大将在第一轮就杀入敌阵。
然而看到诸多将士奋勇冲杀,特别是那些在头排第一的甲兵,个个身被敌血,有好多个已经看不出衣袍甲胄原本的颜色,只看到一个个血人般的甲兵在继续挥击向前,将对方松散的阵列打出了极多的缺口,更多的矟手沿着锐士打开的缺口继续前行,亦有锐士阵亡,被多名海盗同时袭杀,有个锐士便是被多支长枪刺中,长枪从铠甲的缝隙中穿透过去,或是刺穿顿项,那个锐士顿时就该气绝了,但居然屹立不倒,稳稳的站在原处,其后的甲兵都绕过他,别的海盗看到如见天神一般,只由着那个浑身浴血的锐士稳稳的站在原地,四周是伏尸遍地,鲜血横流。
这是相当壮观和壮烈的景像,南安府军象是世间最为锋利的锥子,一下子就刺破了敌人的防御,在宣布进军的同时,顷刻之间,鼓声激昂,无数面红旗招展挥舞,将士们奋勇向前,一浪接着一浪的拼力往前攻击,敌人的阵列瞬间被打穿了,整个天地之间仿佛都变色了,战场上黄色的尘土都象是被灰色的府军狂潮给压制住了,随着数千将士奔腾而下,那些铁制的兜鍪,铠甲,兵器,象是阳光下反射的湖面,发出波光闪闪连绵不绝的光芒。这光芒无比耀眼,也无比强大,此情此景,令人感觉山河变色,天地颤栗,连那往常叫人感觉天地伟大的茫茫大海,在此时此刻都变得无关紧要了。
而看到府军冲击之态,看到将士一往无回的冲向敌阵,看到那屹立不到的浴血将士,看到继续向前,奋勇杀敌的府军将士们,天地之间,又有什么军阵能够横亘于前,挡住府军将击的攻击呢?
海盗们越来越难于抵抗了,对面的人确实是少,但他们的兵力虽然是府军的好几倍,却根本没有摆开象样的阵列,而且他们的兵力相当的分散,被拉扯的太长。
在海边上岸,并没有建立营寨,亦无需考虑后勤,只想着一阵破敌,海盗们根本没有后续抵抗的能力和应对不利战局的想法。
在前方的阵列被陆续打穿之后,府军将士如雪崩之时的烈日,将眼前之敌炙烤的无处躲藏,只能纷纷融化逃避,正面之敌开始纷纷避让,逃窜,灰色的府军在杂色的海盗群中形成了显明的颜色,强行融入,并且越来越扩大了追击的范围。
在最危急的关头,颜奇并未后退,他凶悍无比,此时被杀的凶性上来,看到一队队的海盗躲避,逃奔,大量的阵列被打穿,虽然有很多海盗还是相当悍勇,他们不是乌合之众,很多海盗武艺高明,在和府军的对抗中并不吃亏,但他们亏在几乎总是在单打独斗,一个高壮海盗挥用两只短斧,身手异常的矫健敏捷,但前排一名锐士用盾牌架住他,后头三个矟手刺头,胸腹和两腿,这个海盗根本闪避不及,顿时就被长矟透体而过,发出了骇人的惨嚎声。
颜奇见状大怒,他左手持盾,右手持弯刀,开始大踏步的向前而行。
三百余穿扎甲的海盗,亦在阵中推向前方,有挡路的海盗,便是一刀斩杀。
颜奇和他的部下一边向前,一边厉声喝令所有的在一旁的海盗不得退却,继续跟随,向前冲杀。
这三百余人带动着四周的两三千人,聚集成了一个厚实的阵式,开始向着府军的前锋迎击而来。
“取投矛。”看到有大量银光灿然的海盗出现,葛存忠立刻下令投矛准备,这明显是海盗中的精锐,此战的决胜点,应该就在此时。
葛存忠领第二军偏于府军的左侧,他原本的阵列在第二排中间位置,前排的一个队官战死后,第二排的左侧第一人便立刻上前补位,站在了第一排第一人的位置上去。
这个位置毫无疑问是相当的危险,这也是锐阵战法的特殊之处,侵略如火,攻击极为犀利,开战才两刻钟不到,已经洞穿了海盗的多道防线。
要知道这些海盗的个人武艺并不算弱,甚至是相当的强悍,他们拼力反击,锐兵死伤是很正常的事情,而这样的战法却不能停止,前方一人死,后方一兵补上,再后方依次类似,始终会保持着锋锐强大的攻击力。
此战阵前方倒,后方补,前后则以五重为限。
若后方将士连续向前补上五重而不能最终获胜,打溃敌阵,则战事必败无余,也就没有必要考虑五重阵后敌阵不破该怎么办的事情了。
这就是一往无前的冲锋之阵,在敌人出动甲兵之时,也不能叫南安侯府的府军们稍微停滞一下冲锋的脚步。
府军的阵列始终未乱,一人前,三人后,五人再后,一队,一都,一营,直至全军,六千余人是大三角,其中又有无数个小三角。
无数锐士在前,矟手在后,每后牌必有后补锐士,前人亡,后人必将补上,无有人犹豫,亦不会有人后退回顾。
在知道南安侯也到阵中的时候,整个军阵的士气已经被鼓舞上来了,将士们一直在向前冲杀,在刀枪从林之中浴血向前。
在看到敌人精锐尽出时,葛存忠厉声下令,命所有将士以投枪遏敌。
投枪之术,府军早已习之,阵前突破,弓手很难一直跟随,这也是弓兵不足之处,防护不力,肉搏之术不足,若携长矟大刀,则难携长弓插袋,若披重甲,则难以挽弓施力,所以一般弓手着轻甲,带胡人用的那种小刀,很难自保,聊以做心理安慰罢了。
此时便是如此,锐阵两翼的弓手并不能直接与箭头前锋一直向前,逐渐落后,开始射箭扰乱海盗两翼。
而前锋遇敌,便要依赖投矛对敌了。
每兵皆在身后带投矛数支,一声令下时,对面的颜奇已经部部赶至,其部下阵列亦很森严,特别奇异之处并不是身上磨出银光的扎甲,而是人人均持有的天方长剑和弯刀。
天方人擅长用驼驼骑兵,北虏兴盛时曾经破天方诸国,一直攻入巴格达等地,天方国势严重受挫。
但天方败而不亡,主要是其地方炎热,北虏骑兵是从高原苦寒之处下来的,不管人和马均畏惧酷暑,而驼骆骑兵则耐旱,在干旱的,千里无人的沙漠中如履平地,双方交战,北虏尚未战已经先输一筹。
及战时,天方人骑驼骆或天方马呼啸而至,彪悍绝伦,除了骑射之法不强于蒙古骑士外,骑术,战法,铠甲,俱不在蒙古骑兵之下。
而地利,马,驼骆,铠甲,甚至天方人优于蒙古人。
当时的天方骑士,用长矛等长兵器少,其弓箭亦不见长,所长者就是用天方剑,骑兵冲杀时,依靠铠甲和锋锐无比的天方剑对敌,居然屡次击败蒙古骑兵,终获胜利,不仅将蒙古人驱离天方境内,更越葱岭前行,从黑山口等多处地方越境而入汉时西域,占了大片盆地和南方的沙漠绿洲区域,将原本羌人,回鹘人,吐蕃人,白兰人俱归化了天方教,成立叶尔羌汗国,亦就是与大魏相峙多年的西羌。其与莫卧尔,帖木尔诸国,皆成天方属国,经过挫折之后,反是因祸得福,因为极剧膨胀中的北虏在大魏这边失败,失去了对幅员万里疆域的掌控,反是叫天方人跟在后头捡了便宜。
颜奇手中的弯刀,是近几十年来天方骑兵所用弯刀,是其奴隶骑兵擅用的骑刀,这种奴隶骑兵从小就被养育在一起,会走路时就接受最为严格的战技和骑术教育,他们的刀也是最高明的工匠用最好的钢锻打而成,就算是蒲行风的身份也只能给颜奇几十把而已。
三百余人的扎甲军,用几十柄钢制弯刀,二百多把天方直剑,拥众向前,颜奇走在队列正中,群盗相随于两侧,众多人开始再次吼叫和呐喊,试图将被府军打落的士气再度鼓舞起来。
与此同时,刘旦率部在左侧加快了行军的速度,中路纠缠交战,海盗阵列摆开的很广,尽可以用左右两边的军阵包住魏人的侧翼,从三面一起攻打,魏人的军阵虽然犀利,但对左右翼缺乏保护,只要兜转过来,胜利便在眼前了。
极品粉嫩白丝少女一线天馒头国产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