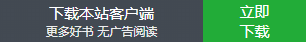第三百四十九章 乘风破浪
五月十七前后,陈笃竹得到了相当明确的信息,东藩那边的储盐超过了三万石,堆积如山。
按大魏官盐四十文一斤的价格,东藩盐也完全配的上。
一样的细密洁白,甚至比官盐犹有过之。
毕竟大魏的吏治开始崩盘,从转运使到盐仓大使都在上下其手,官盐不仅价格越来越高,质量也是一步步的开始下跌。
东藩盐价的包销价是十六文一斤,零售价是十八到二十文一斤,低于官盐一倍还多,比有的私盐价格还要略低一些。
这是一种倾销策略,新的盐出现,迅速打开销路,挤掉原本的私盐市场,在最短时间内把大量的私盐市场给抢下来。
官盐当然也会受影响,南安侯府那边已经定下策略,尽可能的在乡镇村庄出售,大批量的分销给小商人,很多地方原本就不是官盐的受众群,就算买盐也是买私盐或黑粗盐,这样对官盐的影响会减弱减低。
盐税不可能不受影响,但在朝廷层面也就是几十万贯到百万贯左右的减收,还在能容忍的范围之内。
一亿多贯的收入,减低几十万贯或百万贯的收入,安抚的是徐子先这样的一方国侯重镇,这笔帐两府还是算的过来。
在几个路随便找个名目开征几样杂税,把酒醋钱加征几文一斤,这亏空也就弥补回来了。
这么多年一直是这么做的,从来没有例外。
而且随着北伐的进行,天子的封桩库也如冰雪般在消融,崇德皇帝一直生活俭朴,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把贡入大内的钱财贡物收藏起来,准备用在北伐的大事上。
从这一层面来说,崇德天子的私德甩开成宗皇帝一百条街。
但北伐的用度肯定是封桩库负担不起的,更进一步的大规模的加税势在必行,引起动荡,不满,乃至群盗并起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这种都面下,盐税上的小小波动,根本不会被中枢看的太重。
陈笃竹对此都面有着清楚的认识,他是昌文侯府的疏宗,也就是说在公中获得的钱粮支持是相当有限的。
昌文侯府当然有公田,有祠堂,有族学,最疏远的族人也能获得免费教育,侯府会帮着下葬那些贫穷的族人,不至于叫族人被放在义庄里无处安葬。而且有公田,那些老弱和孤儿都会被奉养,贫困家庭会得到公田的帮助。
但要想出人头地,无非就是在族学里读书,只有读书才是最好的出路。
如果读不出书,而又聪慧过人,那就是帮宗族奔走忙碌这一条路可走了。
三十年来陈笃竹奔行大江南北,行走了几百个军州,所行所见至今,他深感大魏已经是积重难返。
多日前他和昌文侯陈笃敬会面密谈的时候,对方也是证实了他的这个见解和看法。
大魏风雨飘摇已经好几十年,但有多难的关口都能闯过来,似乎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发生,但能在蛛丝马迹之下发觉那颗朽木快要支撑不住,这才是陈笃竹这一类人存在的意义。
况且他也不光是掌管昌文侯府对外生意买卖的事,事实上和本路士绅的交往联系,两浙,江南的官绅和大豪商之间的联络,亦是陈笃竹在主持。
在此之前,昌文侯府和南安侯府在福建路的利益一致,两家是姻亲和生意合伙人。
但在北伐之后,都面演化之后该如何处理两家的关系,另外还有怎么影响那些遍布各路的官绅商人势力,这才是陈笃敬和陈笃竹等人要考虑的事情。
“竹兄来的早。”林养先从一顶二人抬的小轿上下来,他腰腿不好,不能骑马,就算坐轿子下来之后也是一直不停的在捶打自己的腰眼。
“只能坐大哨船了。”陈笃竹笑着指一指眼前的小型帆船,说道:“好在这船很快,很快就能到澎湖。”
两人相视一笑,都是感觉这个安排很妙,事实上,他们都急不可待了。
大哨船长十米,宽三米,要是在江上或是沿岸,带上三五十人也不在话下,原本就是厢军用来巡防哨探用的小船,船有单桅或双桅,前桅稍许前斜,升降帆索很快,吃风很快,船体轻,有四桨一橹配合,在岸边划动,借助风力,船行如飞。
从福州出发而不是从漳州,海程稍远一些,但坐着小哨船出发,半天都不要就可抵澎湖,一天时间足以抵东藩。
两人上船之后,发觉船下还有十来个工匠,众多工匠知道这两位是老爷,都是站起身来行礼。
“尔等去东藩何事?”陈笃竹摆了摆手,示意众人坐好,这时船身震动,已经起锚出发。
“我等去东藩去营造工厂。”一个工匠叉着手道:“那边在河边水流边建工厂,匠人不够用的。”
“窑夫、冶夫、瓦匠、石匠、铁匠、木匠,木匠分水、旱木匠,又有高木匠、低木匠,大作、小作之分,皆可,我等有瓦匠,有高木匠,大作,低木匠,那边都是开了四贯钱一个月的工钱,算来比在家没多赚多少,但东藩岛上不对匠人收税,是以小人们都愿意过来。”
一个高手匠人,特别是高木匠,水木匠,还有铁匠,一个月赚五六贯钱都是相当正常的事情,毕竟他们每天都要揽活做,相当辛苦,而且有着高超的手艺。
大魏又没有如明朝那样把匠人弄成世袭的匠户,世代相袭,把匠人当国企工人看待也没错,但缺乏物质激励,所以明朝匠户,特别是军匠都生活的相当凄惨。
而大魏的工匠都是雇佣制度,哪怕是官府,只要不是服徭役,官府的工程也一样要花钱雇佣工匠,不能强征。
清朝时的情形就是比明朝还要过份的多,乾隆年间英使团到达浙江沿海后,因为不熟悉中国航线,英国人请求当地总兵帮他们找一个领航员。总兵痛快地应答了,而英国人却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总兵强迫百姓引路。
总兵的办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从海路去过天津的百姓都找来。
使团成员巴罗说:“他们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带回了一群人。他们是我平生所见神情最悲惨的家伙了,一个个双膝跪地,接受询问。他们徒劳地哀告道,离家远行会坏了他们的生意,给妻子儿女和家庭带来痛苦,总兵不为所动,命令他们一小时后准备妥当。”
而在眼前,小哨船上的工匠们,他们虽然谈论起沉重的赋税时也感觉不满,甚至对朝廷都失去了信心,甚至对官家也不再那么尊敬。
但他们是自得的,自尊和自信的。
他们相信自己的手艺能养活自己和家小,他们确定自己被需要,也不是在操持什么贱业。
更不可能会有一个武将随意一指,一群如狼似虎的官兵过来将他们抓走,连饭钱和路费都不给,就叫他们当几百里上千里的纤夫,或是向导。
这在大魏是不可能的事。
在汉,唐,宋,在华夏王朝的正常时期,而不是作死的末世,不需要是盛世,只是普通的时候,比如唐高宗时期,中宗,睿宗,或是明朝的英宗,宪宗时期,服徭役要有手续,要考虑到细民百姓的生活,农忙时不征,农闲时才会征调徭役。
工匠服役要有时限,不能无止境的征发徭役,要体恤民力。
一切都要有规矩,官员不能为所欲为。
当然最好的王朝也会有黑暗面,也会令人厌恶,当有人忍受不下去时会举起义旗,再来一次王朝更迭。
眼前这些工匠,他们就饱含着期望,轻一点的赋税,更好的待遇,更高的收入,能使妻儿过的更好。
这是一个正常的国度,尽管它在生病,肌里腐烂,变得不再那么友好,不那么富足,很多人生活的很辛苦,甚至是痛苦。
但它还是一个正常的国度,它没有把百姓当奴隶的想法和理论支持,士大夫们有自己的想法和操守,天子想扶持自己的亲信与两府对抗,配合的文官都并不多。
大家很喜欢功名富贵,但也要讲一讲规则和名誉,彻底的把自己当奴仆,把皇帝当成亲爹来伺候,这实在是办不到的事。
小哨船出了港口,飞速向前,犹如飞鱼船在海面上飞掠而过,剪开浪花,不断向前。
“午前至澎湖,停船一刻,搭几个人上船。”船行至午前,哨船的船长对众人道:“两位老爷和诸位匠人都是去东藩,澎湖有几位老人家也是去东藩,我们过来时经过澎湖,已经说好了去带他们。”
“无妨。”林养先倚在船帮上,浪花时不时的涌到船身里来,将他袍服都打湿了,不过身为常出外的人,对这些事早就习惯了,当下只是含笑道:“小事情,我们也知道这小船是南安侯府的船,你们都是水师将士,辛苦诸位了,回头到东藩,给你们些酒钱去喝酒。”
“多谢。”船长笑着一抱拳,说道:“按咱们南安侯府的规矩不能收两位老爷的钱,到了东藩,可以请岸上的人帮着带路,或是雇佣车马骡驴,岛上开发出来的面积也不小了,也有商人办了脚行车行,放心,咱们南安的规矩大,那些车夫脚夫不敢乱来。”
船长确实是个军人,林养先和陈笃竹都注意到对方身上一袭蓝色的武袍,衣袍裁剪的很合体,显露出腰身,不象普通的大魏百姓,就是将一块布裁剪出几个洞,往头部一罩就算是袍服了。
就算是士人老爷们的袍服,也是没有什么真正的裁剪,无非就是讲究布料。
眼前这些水师官兵虽然不是宽袍大袖,衣料也是最普通的粗布,无非是更加厚实,但裁剪的相当好,林,陈二人不懂,这是设计的功劳。
合体的衣袍,袖子都有铜扣固定,腰间有革带束紧,长袍至膝前,下身长裤,骑兵和军官是马裤,军官们是长靴,士兵们是短靴,在海上则穿麻履,因为不容易滑倒。
眼前这些水师官兵,着装利落,漂亮,说话得体,脸上和身上都透露出一种相当乐观,沉稳,健康的感觉。
林养先年过五十,他想了想,似乎自己少年时的大魏禁军,差不多也是眼前这些军人的感觉。
大魏禁军也很不错,待遇很高,赤红的军服也很漂亮,几百个禁军聚集在一起时,宛若聚拢的红云。
薪饷高,待遇不差,家小都能被养活的不错,加上四处太平,禁军的地位并不低,大魏从来没有过重文轻武,更从来没有把军人将成囚犯,那种在军人脸上刺配的做法在唐末有不少节度使做过,大魏太祖直接废除了此法,只有良家子才有资格入禁军,身高,体貌,还得加上无犯罪纪录。
曾经的骄傲和光荣已经不复存在,林养先神色有些复杂,一个人的经历决定了他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向,不管南安侯府的府军怎么精锐和有着蓬勃生气,林养先还是宁愿眼前的是大魏禁军。
少年时记忆里的大魏禁军,强大的军队,英明爱民的官家,运作良好的朝廷,驭民爱民的官员,兴旺的工商贸易和富裕满足的百姓。
晚上天黑时,城镇和乡村到处也有灯光,妇人们带孩子,男子们脸上长着肉,眼中是高兴的光芒,三五成群聚集在一起,到集镇和村庄的小酒馆要上几个菜,三五人喝酒吹牛,借此卸下满身的疲惫。
那时候城市里有运作良好的养济院,漏泽园,济慈院,慈幼都,鳏寡孤独俱有所养,无有流民饥民和无人奉养的老人,孩童。
林养先闭上了眼睛,将身体轻轻倚在船身上,小哨船晃动着,继续乘风破浪。
舒淇、翁虹、温碧霞早期全裸电影无删减免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