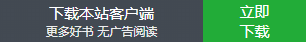第一千七百一一章 掀桌子了
“我哪管得了这种事?”
李孝恭连连摇头:“我这身子骨也熬的差不多了,帮忙筹办丧事便累得够呛,还不知活到哪天呢,哪还有人听我的话?谁爱闹谁就闹去,自有国法家规等着,今日二郎处置的就很是合适,谁敢闹事就抓起来让陛下裁决,看他们谁还敢闹?”
几人都无语,心中腹诽,若是当真怕陛下他们就不敢闹,既然闹了自然就是不怕……
不过也听得出这位“宗室第一郡王”心灰意懒之意,如今宗室里闹闹哄哄、人心不稳,掺和进去弄不好就要栽个大跟头一世英名尽付东流,置身事外才是明智之举。
况且有李神符这位宗室耋老扯大旗,李孝恭的威望大打折扣……
或许是李元嘉离开的缘故,作为家主的李道立终于姗姗来迟,只不过鼻青脸肿颓然神伤的模样着实令人不敢恭维。
几人起身相互见礼之后分别落座,李孝恭关切问道:“伤的可还严重?”
李道立叹口气,摇摇头:“不过是皮外伤而已,先前因为心情悲痛神志恍惚故而在京兆府衙门犯了混,实在是丢人现眼。韩王殿下呢?我得给他道个歉。”
房俊笑吟吟道:“我是韩王小舅子,您可以向我道歉,我替他收下,回去转告给他。”
在你家里你难道不知李元嘉已经告辞了吗?如果当真有担当刚才就应该出面说两句场面话道个歉,而不是现在人家都走了你出来说敞亮话。
李道立瞪眼看着房俊,对于这厮不给自己台阶下很是恼火。
李孝恭打圆场:“都是自家兄弟,偶尔有些矛盾自是难免,吵一场打一架到此为止,切不可被外人看了笑话。”
李道立点点头:“叔王说的是,先前是我冲动了,不该与韩王那般无礼,待到吾儿丧事结束定会亲自登门赔礼道歉。”
李孝恭很是欣慰:“关于景淑之死我亦深感悲痛,只不过人死如灯灭,既然元凶已然伏法那这件事就这样吧,回头我去宫里见见陛下恳请对元凶予以严惩,可令逝者安息。咱们活着的终究还是要好好的活下去,不可沉溺于对逝者的缅怀当中不可自拔,否则景淑地下有灵也必然愧疚失望。”
“哼!”李道立冷哼一声,睨了戴胄、刘祥道一眼:“世间事真真假假、虚实难辨,前一刻凶手已然抓获,后一刻真凶却又另有其人……三法司果然秉公执法、公平公正,既不冤枉好人、也不放过坏人,本王佩服得五体投地。”
这话里的冷嘲热讽毫无掩饰,戴胄与刘祥道都有些尴尬,毕竟素来以公正著称的两人从未想过平生少有的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之事,居然实在陛下的授意下去办的。
到了他们这个位置,早已摆脱了单纯的“公平公正”,律法需要为朝局的稳定和谐让步,陛下既然要求“既能分化襄邑郡王团体内部、又避免宗室与韦家直接冲突导致局势动荡”,那就只能将韦叔夏摘出去减轻罪责。
虽然事实上韦叔夏的确不构成致死韦叔夏的“真凶”,但任凭韦家将罪责甩给无辜的柴名章,却是彻彻底底的“枉法”……
既然心虚,坐下去自然尴尬,两人同时起身:“一大早便操办公务整整一日未曾得闲,实在是浑身乏力、精力不济,吾等暂且告退回家歇歇,明日下值再过来。”
李道立毫不客气:“寒舍实在当不起两位贵客,快去忙着如何颠倒黑白、如何枉法裁判吧,你们坐在这里我怕吾儿之魂灵不安,跑出来找你们麻烦。”
戴、刘两人无话可说,施礼之后匆匆告退。
出了门,两人对视一眼,齐齐叹了口气,戴胄低声道:“为官半辈子虽然不敢自诩清如水、明如镜,却也心境坦然无愧于这一身官袍,孰料临老却办了这么一件事弄得声名狼藉心中有愧,唉,奈何,奈何。”
之所以说出“奈何”是明知此事有悖于律法却不得不按照陛下的意愿去办,朝局稳定了,宗室内部的分化也达到了,只不过牺牲掉的却是自己的名声与理想。
刘祥道白了他一眼,不满道:“你不过是大理寺卿而已,办好办差其实也没什么,为官一任纵有瑕疵旁人也能理解。我可是御史大夫啊,朝野上下排在第一的清流名望,可以辞、可以贬、甚至可以死,却唯独不可以徇私枉法……你觉得心里苦,我心里这苦水又向谁说?”
戴胄捋着胡子,心里居然舒坦了一些。
退一步讲,这件事最终若是爆料出去,自己或许也只是获得一个“不够忠直”的评价,而身为御史大夫的刘祥道怕是就要遗臭万年了……
所以说世间事“不患寡而患不均”,原本自己觉得郁闷,现在见到刘祥道比自己还惨,居然也不是那么郁闷了……
刘祥道再叹一声:“惟愿自此风平浪静吧,让咱们的付出能够有些价值。”
戴胄闷声道:“怕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
两人再无谈兴,拱手施礼各自登车,恰好府邸分属东西,故而车架背道而驰……
……
李孝恭与李道立闲聊,后者不停抱怨三法司审判不公,房俊喝着茶水觉得无聊透顶,既然已经前来吊唁算是没有失礼便足够了,两家只有仇怨没有交情,遂打算就此告辞。
未等起身,便见到郡王府的管事领了一群人进来,正是大大小小一群驸马……
薛万彻第一个进来,略微抱拳向李孝恭与李道立失礼便一屁股坐在房俊身旁座位,等不及侍者奉茶便拿起房俊的茶杯一饮而尽,吐出口气,将领口略微松了松,大大咧咧抱怨道:“这长安城是没法待了,白天太阳晒、晚上如蒸笼,唯有泡在水里的时候凉快一些,从水里一出来便一身汗黏黏糊糊,太遭罪了。”
执失思力也顺势做过来,闻言笑道:“听说薛家在神禾原有处庄园,背山临水风景秀美最是避暑的好去处,何不带着公主出城去小住几日?”
薛万彻一脸烦躁:“你以为我不想啊?可这长安城里今儿闹事明儿死人哪有个消停的时候?想走也走不开啊!一个两个的放着好日子不过成天出幺蛾子,都特么活腻歪了!”
李道立怒目而视,我家办丧事呢你说这话合适么?
他却忘了薛万彻何许人也,会管你这个?
薛万彻的眼珠子瞪得比李道立还大,大声嚷嚷:“瞪我作甚?我说的就是你!捡了个郡王的爵位就应该偷着乐,老老实实钟鸣鼎食作威作福,非得掺和那些个不臣之事不就是茅坑里打灯笼找死呢?儿子死了你就是活该,方言瞅瞅都是在笑话你的,哪有半个人同情你?”
一起进来的有高祖皇帝的驸马乔师望、苏勖、郑敬玄等,还有太宗皇帝的驸马刘玄意、王大礼、柴令武、杜荷等,听到薛万彻的言语都齐齐愣住,很是尴尬。
虽然这厮说话皆乃事实,可今日这场合总得给东平郡王府一些颜面,嘲笑李道立瞎折腾也只能在暗地里,岂能直斥其非?
李道立气得火冒三丈,一把将头上裹着伤口的纱布拽掉就待冲上去跟薛万彻拼命,被王大礼、杜荷等人拦阻,纷纷出言劝说。
李孝恭也无奈,呵斥薛万彻道:“说什么浑话呢?整日里正事不干就知道胡混,嘴上连个把门儿的都没有,简直不像话!”
旁人害怕这位“宗室第一郡王”,薛万彻却是不怕,梗着脖子反驳道:“郡王这话可说差了,我怎地就整日胡混了?我是个浑人没错,可我知忠义、懂廉耻,我家与太宗皇帝有仇,可我从拜倒在太宗马前那一刻起便唯命是从,关陇兵变的时候贼军浩浩荡荡翻天覆地,唯有我宁死也站在太宗皇帝身边!太宗皇帝驾崩,陛下登基,晋王兵乱,还是我旗帜鲜明的拥护陛下,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反观此间诸位,您让他们一个个拍着胸脯扪心自问,是对太宗皇帝忠贞不二还是对当今陛下誓死效忠?”
房俊目光炯炯、兴致盎然,好家伙,一杆子将屋子里所有人都给干翻了。
关陇、晋王连续两次兵变,无论宗室还是勋贵都各有计较,明面上支持太宗皇帝、当今陛下,实则暗地里与叛贼暗通款曲者比比皆是,这事儿就连李承乾也心知肚明却没办法计较,大家也都装糊涂把这件事揭过去,薛万彻却口不择言当众说了出来。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当所有人都选择沉默的时候,明明发生了也可以当做没发生;可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将事情挑明,那么就不能继续当做没发生。
他不认为薛万彻具有掀桌子的智商,那么此刻看似义愤填膺口不择言又是谁在背后指点他呢?
最为严重的是此间言论发生,陛下又将以何等态度去对待那些曾经在暗地里背叛他的宗室、勋贵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