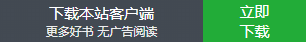第一千四百二十四章 反戈一击
面对李义府咄咄紧逼,房俊依旧岿然不动、神情淡然:“是非曲直,自有公论。房家湾码头每一寸土地皆乃由房家出资购买,文书、地契皆一式多份,分别由买卖双方及京兆府备案,谁有质疑,可随时查阅。”
他只解释了关键的地皮归属权问题,却没有提及李义府弹劾的“来历不明之人口”,这些年大唐南征北战,尤其是水师纵横大洋灭国无数,间接或直接控制的东洋、南洋番邦不计其数,人口贩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诸如突厥人、新罗婢、昆仑奴都是整个大唐都极受欢迎的“产品”,相比于被世家门阀以及整个帝国视为根本的大唐百姓,那些外洋贩卖而来的奴隶又勤快、又廉价,谁能不用呢?
这些奴隶是不可能逐一在官府衙门里备案的,往往备案一个,私底下却贩卖十个,只要有一个名目上的交税就足以,民不举、官不究,视作常态。
说到底,这些东西都是见不得光的,解释不清楚。
然而话说回来,这种事早已形成潜规则,纵然房俊有所触犯,也当不得大事,只要不曾私豢汉人奴隶,顶了天就是罚金抵罪。
但是很显然,正所谓集腋成裘、聚沙成塔,单一罪状或许不能扳倒房俊,但十件、二十件呢?
李义府申请有些亢奋,站在太极殿上,背对群臣、面对皇帝,慷慨激昂、指点江山,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成就,今日虽然只不过作为御史台推出的“一把刀”,却也让他体会到了站在帝国最高权力机构的感受。
令人着迷……
李义府昂首挺胸,言语铿锵:“此次封堵潏水决口,处置尚算及时,严格来说工部衙门无过有功,毕竟是天灾嘛,防不胜防……然则越国公在人口匮乏之时却悍然调动玄武门外驻军,未曾觐见请示陛下,也未曾经过军机处商议,更未有兵部公函下发……此举固然使得决口尽早封堵,却使得军国社稷处于危险之中,犯下的乃是夷灭三族之罪!陛下明鉴,微臣自然不认为越国公有谋逆之心,但这般私自调动军队若是不予以严惩,日后人人效仿之时,君王安危何在?社稷安危何在?还请陛下颁旨,诏令三法司审查此案,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殿内落针可闻,无论哪一方、哪一派,在李义府弹劾房俊“私自调动军队”这一项罪名之时,都紧紧闭上嘴巴。
这件事可大可小,如果李承乾觉得房俊有“功高盖主”之嫌,那么趁此机会打压房俊、收拢兵权正当其时,谁敢沾边谁就要被被卷入其中粉身碎骨的觉悟;反之,若陛下对房俊信任依旧,当真存着“朕与爱卿共富贵”的初衷,那么这就不算事儿。
毕竟房俊私自调兵乃是为了赈济灾情,不算公器私用……
但是谁知道陛下心中怎么想?皇帝这个职业可以使得人心狭隘、猜忌日重,“伴君如伴虎”可不是说说而已,当年胸怀四海。英明神武的李二陛下到了晚年之时,不也是喜怒无常?
李承乾面色如常,似乎并未察觉到他此刻需要以如何回复李义府来表达自己对待房俊的态度,拿起茶盏喝了一口茶水,淡然问道:“可还有没有?”
李义府:“……”
已经将最为重要的“私自调兵”放在最后作为压轴,这还不够?
“陛下明鉴,上述之事已经由御史台仔细甄别、调查取证,俱属事实,置于其他一些罪状不过捕风捉影而已,暂时尚无实证,故而御史台暂且不予弹劾。”
“嗯,越国公可有什么解释?”
诸位大臣的目光都看向房俊,却见到房俊并未开口,而是自怀中掏出一摞奏疏,目测有七八份之多……
一部分大臣疑惑不解,这厮是早已针对自己被弹劾之罪状分别写好了辩解之词,亦或是请罪的奏折?总不能老老实实就认罪吧?
但有一些贞观朝的老人却恍惚间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久违的记忆涌上心头,顿时面色大变,尤其是一些难言清白之人更是一个个瞪大眼睛,心脏不争气的飞快跳动,忐忑不安。
这棒槌又来这一招?
可求求你了,别扩大打击面啊……
然而越是怕什么,越是来什么。
只见房俊捧着一摞奏疏翻翻看看、挑挑拣拣,从中取出一份递给一侧的内侍,大声道:“陛下,微臣弹劾李义府忘恩负义、贪墨公帑、徇私枉法、栽赃构陷!此人当初参加科举考试,穷困潦倒、衣不遮体,微臣适逢监考,见其可怜遂以衣物相赠,无论如何都算是照拂之情,孰料此人之后非但不记得赠衣之情,反而对微臣恶语中伤,是为忘恩负义!担任万年县令其间,以各种瞒报、谎报、私吞、挪用等等手段共计贪墨公帑三万余贯,区区一介县令广置房产、生活豪奢、婢仆如云!更可恶者,包揽诉讼、制造冤案、收受贿赂、操纵国法成为其敛财、徇私之手段!对微臣恣意构陷、随意栽赃,看似微臣各项罪证确凿,实则捏造事实、捕风捉影,请陛下治其死罪!”
大殿之上群臣哗然,纷纷交头接耳,看着不知所措的李义府,议论纷纭。
分明是代表御史台站出来弹劾房俊,孰料被房俊反戈一击,反过来弹劾?
而房俊这一手当初也曾使过,不知多少文官试图将这个“佞臣”扳倒,结果反被房俊弹劾,最后房俊岿然不动、青云直上,那些弹劾他的官员却是要么降职外调、要么丢官罢职,甚至锒铛入狱、前程尽毁……
李承乾接过内侍递来的奏疏看了看,便用力一丢,丢在李义府脚下,冷声道:“你有何话说?”
李义府有些懵,赶紧蹲下捡起奏疏,一目十行的看过,心底一股股寒气升腾而起,打了个冷颤,只觉得脑袋轰然作响,面色惨白。
奏疏之上,除去言及他忘恩负义、栽赃构陷之外,还有他担任县令之时一笔笔贪墨的钱粮数目、明细,虽然他自己也记不得如此清楚,但其中有几项却还是记得的,也印证了这份奏疏并非胡言乱语……
可问题在于哪一个官员能真正做到清如水、明如镜,两袖清风、纤尘不染?
有一些东西的确是贪墨了的,但却是官场之上所默许的规则,几乎所有人都那么干,甚至就连房俊也未必就能一针一线没占过衙门的便宜……
所谓徇私枉法更是夸大言辞,万年县令虽然只是区区一个县令,却掌管着半个长安城以及城外数以万计的土地、数以十万记的百姓,固然比不得当朝宰辅、封疆大吏,却也不折不扣算是一个权力极大的官员,等闲时候总有一些人情需要往来,长安城内的达官显贵们一旦涉案,谁能保证全部公事公办?
你还混不混了?
有一些案情并不明朗或者证据并不充分的案件,权衡涉案双方之后区别对待是难以避免的,即便是当年铁骨铮铮的魏徵也做不到一碗水端平……
可现在看着奏疏,那些事情具陈其上,让李义府心里一阵阵发凉,寒毛都竖起来了。
这明显是有人一直在盯着自己,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难以逃脱那黑暗之中的眼睛……
不需问,必然是房俊无疑。
李义府手里哆哆嗦嗦的捧着奏疏,抬头看向房俊,不可思议道:“越国公……何至于此?”
说他“忘恩负义”,他断然是不肯承认的,是他没有因为“赠衣之情”主动向房俊靠拢吗?是房俊不要他啊!但凡房俊有一丝一毫收留之意,他纵然是做一条狗也是心甘情愿的,可房俊却怕他这条狗会咬人,一脚踢开。
若非走通了刘洎的门路得以进入御史台担任一届监察御史,他此刻早已被贬斥至天涯海角烟瘴之地,与野人蛮胡为伍了……
可他着实想不通,以房俊之权势、地位,为何这般欲置自己于死地?
瞧瞧房俊自踏入官场之后的对手,以前是权倾一时的长孙无忌,现在是文官之首的刘洎,自己不过一个监察御史,芝麻绿豆一样的官儿,没道理啊……
房俊却看也不看他,低头在奏疏之中翻找的动作让不少人心惊胆颤,而后又抬起头,看着御史台那一帮人的方向,问了一句愈发令人心胆俱裂的话语:“刚才站出来弹劾我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御史台一群人除去刘祥道低眉垂眼一言不发,余者皆面色如纸、两股战战,闭着嘴巴不吭声。
这年头那又什么两袖清风?说到底都是世家子弟,出仕为官皆乃家族支持,为官之后自然要想法设法反哺家族,经手的权钱交易不知凡几,如何谈得上清廉如水?
而房俊显然有着无与伦比的消息渠道,能够轻易得知不少官员背后的秘辛,万一这厮捧着的奏疏之中便有自己一份,那岂不是自寻死路?
到了这时,御史台诸人也隐隐明白过来,刘祥道之所以主张弹劾房俊,并非多么公正无私、维系纲纪,而是想要借由房俊之手,剪除御史台内的不同声音,没见到刘祥道自己以及他的心腹对于弹劾房俊具体之事一言不发、置身事外?
偷吃小姨子视频漏出